
標題

標題
內(nèi)容
謝有順:文學批評要有生命的學問做底子
更新時間:2017-06-06 來源:中國作家網(wǎng)
原標題:謝有順的文學批評之道:“經(jīng)驗作者的經(jīng)驗,理解作品中的人生進而完成批評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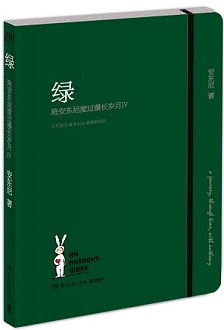

2017年4月28日,作為第二屆華語青年作家獎的重磅評委之一,謝有順受邀來成都參加了該獎項的頒獎典禮。不管是來自全國各地出席典禮的青年作家,還是四川本地文學圈的作家,見到謝有順,都有一種親切的敬佩感。找他簽名,邀請他寫書法留墨寶。面對如此鮮活、靈動、豐神俊朗的白面書生,人們很難不產(chǎn)生好感。而這一切欣賞和好感的背后,正是對謝有順一流的文學才華的認可。謝有順的文學批評文章,在朋友圈被同道同行熱傳,人們佩服他的洞見,又驚喜他的行文氣質(zhì),感到一種心靈的暢飲和精神洗禮之感。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能大概分享一下您關(guān)于文學批評的見解嗎?
謝有順:以一種生命的學問,來理解一種生命的存在,這可能是最為理想的批評。它不反對知識,但不愿被知識所劫持;它不拒絕理性分析,但更看重理解力和想象力,同時秉承“一種穿透性的同情”,傾全靈魂以赴之,目的是經(jīng)驗作者的經(jīng)驗,理解作品中的人生,進而完成批評的使命。所以我所夢想的批評,它不僅有智慧和學識,還有優(yōu)美的表達,更是有見地和激情的生命的學問。只是,由于批評主體在思想上日益單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批評家普遍不讀哲學,這可能是思想走向貧乏的重要原因),批評情緒流于激憤,批評語言枯燥乏味,導致現(xiàn)在的批評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變得表淺、輕浮,沒有精神的內(nèi)在性,沒有分享人類命運的野心,沒有創(chuàng)造一種文體意識和話語風度的自覺性,批評這一文學賤民的身份自然也就難以改變。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從您的文章可以看出,您對鄉(xiāng)間故土的依戀。現(xiàn)代化、城鎮(zhèn)化對農(nóng)業(yè)社會的巨大沖擊,讓很多有鄉(xiāng)村背景的人有一種創(chuàng)痛感。很多寫作者開始了自己的書寫。從整體觀察來看,您如何評價這種書寫?您本人作為寫作者,感到自己有責任作出自己的書寫嗎?您作為一個文學的專業(yè)研究者,對文學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和高度的熱情。對于自己的寫作,您有怎樣的愿景?
謝有順:盡管現(xiàn)在的新作家,很多都出自都市,但在血緣上,多半還是植根鄉(xiāng)土;離開了鄉(xiāng)土,就無從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費孝通說,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其實就是一個超大型的鄉(xiāng)土社會。確實,無論城鎮(zhèn)化的進程如何迅猛,從本質(zhì)上說,中國的國族精神還是鄉(xiāng)土的:社會規(guī)則的建立,多和鄉(xiāng)土的倫理有關(guān);每年清明、春節(jié)大塞車,大家多是往鄉(xiāng)下去;最動人的文學描寫,也多是作家關(guān)于鄉(xiāng)土的記憶。中國文學中,最好的作品,都是關(guān)于鄉(xiāng)土敘事的,這種鄉(xiāng)土資源里,隱藏著一整套關(guān)于中國人生存的解釋方法。這是極為重要的認識尺度,離開這個尺度,對中國人的描述就可能是殘缺的、表淺的。我們這塊土地有如此深重的苦難,也有如此燦爛的榮耀,這么多人在此生生不息,活著,死去,留下了太多的故事,也留下了太多的嘆息,可在現(xiàn)有的書寫者中,還遠沒有寫出真正震撼人心的故事,也還沒有挖掘、塑造出這塊土地上真正得以存續(xù)的精神。二十世紀來,中國的文學多是揭露、批判,寫法上也多是心狠手辣的,它對黑暗和局限的描寫,達到了一個深度,但文學終究不僅是揭露的,不僅是對黑暗的認識,它也需要有憐憫和希望的聲音,也需要探求福克納說的“人類永垂不朽的根源”。就我個人而言,我很想為自己的家鄉(xiāng)寫一兩部書,相信記錄個體的鄉(xiāng)土經(jīng)驗是有價值的。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一個青年作者,要找到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和寫作方向,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有不少人發(fā)現(xiàn),在很多文學作品中,同質(zhì)化的現(xiàn)象,比較嚴重。您作為文學研究者,會怎么說?
謝有順:這令我想起一個“80后”作家對我說的話。她說,我們已經(jīng)無法再進行《紅樓夢》這種百科全書式的寫作了,更不可能像古代作家那樣,細致地去描繪一種器物,一張桌子,或者去描寫一個人的穿著,一次茶聚,一場戲。古代作家由于地域和交流的限制,他所看到、遭遇的經(jīng)驗各自不同,他寫這種有差異的個體經(jīng)驗,誰讀了都會有新鮮感。但是,現(xiàn)代社會不同,現(xiàn)在的孩子,從小到大吃相似的食物,穿相似品牌的衣服,甚至戴的眼鏡、用的文具盒都可能是同一個品牌的,大家的成長經(jīng)驗幾乎沒有什么差異。假若有哪個作家在小說里花很多筆墨去描繪一個LV包,或者講述自己吃麥當勞、法國大餐的滋味,豈非既無聊又可笑?城市化進程,抹平了作家經(jīng)驗的差異,以建筑為例,以前有北京四合院、江南園林、福建民居等地域差別,現(xiàn)在,從南到北,從新疆到海南,房子都建得幾乎一樣,衣服、飲食亦是如此。大家說一樣的話,住一樣的房子,穿差不多的衣服,接受幾乎相同的教育,這樣的公共經(jīng)驗已經(jīng)不足以成為一種寫作資源。所以,寫作如果只靠閱讀經(jīng)驗或書齋里的想象,就容易變得蒼白、無力。我經(jīng)常說,好的寫作,既要用心寫作,還要用耳朵、眼睛、鼻子甚至舌頭寫作,要有豐盈的感覺,作品的氣息才會顯得活泛。同時,經(jīng)驗的同質(zhì),也迫使作家開始轉(zhuǎn)向內(nèi)心的寫作,這反而是好事。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您曾經(jīng)說,當代文學令人興趣越來越小,很大的原因,就在于這些作品所提供的精神容量越來越小。對當下國內(nèi)文壇的寫作者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寫作者,您總體有怎樣的觀察和印象?
謝有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前面幾代作家,幾乎都是通過期刊、評論家和文學史來塑造自己的文學影響、文學地位的,可如今,這個由期刊、評論家和文學史所構(gòu)成的三位一體的文學機制,在“80后”這代作家以及更年輕的作家身上,似乎解體了,代之而起的是由出版社、媒體、讀者見面會所構(gòu)成的新的三位一體的文學機制。而出版社、媒體和讀者見面會背后,活躍著的是消費和市場——正因為這一代作家不回避作品的市場問題,所以,他們的寫作,多數(shù)是讀者在場的寫作,他們不是關(guān)在密室里寫,而是注重讀者的感受,也在意和讀者的互動;通過網(wǎng)絡(luò)、讀者見面會或媒體報道,他們能時刻感受讀者的存在,這個存在,也從正面肯定他們的寫作價值。這當然是一種斷裂,但也絕對是重新出發(fā)。我覺得,他們終將會改變我們對“文學”的固有理解。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在當下,視頻直播、影視作品吸引了年輕人大量的時間,有的是純?yōu)榱藠蕵罚灿袕闹袑で缶癞a(chǎn)品的欣賞的。文學這個事物,應(yīng)該在現(xiàn)代人精神中起到怎樣的作用?有人說,文學未來更多會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在很多載體之中,您怎么看?
謝有順:文學一是讓我們洞察人性的復(fù)雜與豐富,二是建立起人類精神的標高。作家個體的觀察與體驗,永遠是獨特的,不可或缺的。所以,有創(chuàng)造力的文學還會在各類文字藝術(shù)中起引領(lǐng)作用。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影視對文學作品的改編很熱。因此有評論家認為,純文學有一部分要走向市場,通過市場獲得新生。您認同嗎?您有怎樣的觀點?
謝有順:不必刻意聯(lián)姻,但也沒必要拒絕。市場如何,不是作家本人可以決定的,賣得好的書也不是可以預(yù)先策劃的,它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作家不該天天琢磨市場,而該專心寫好作品。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運,但好作品一定會有好的命運。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有一個說法比較常見:這不是一個文學的時代。文學是小部分人的事情。對于文學與時代的關(guān)系,您有怎樣的觀察體會?我們當下處于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種種紛繁復(fù)雜的現(xiàn)象,各種各樣的心靈樣貌。是一個特別值得書寫的時代。應(yīng)該說,這樣的時代呼喚偉大的作品與之呼應(yīng)。但至今好像一直沒有出現(xiàn)這樣級別作品的跡象。您怎么看?
謝有順: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精神的主流、潛流,也有寫作的主流和潛流。我們很容易加入到時代的主流合唱中,寫精神的主流。但我們不能忽視主流之外的潛流,不能忽視一個時代有可能正在發(fā)生的那種細微而又不可忽視的變化。
一個作家如能成為領(lǐng)風氣之先的作家,他一定能率先看到時代內(nèi)部可能發(fā)生的細微變化。如魯迅在他們的那個時代,率先發(fā)現(xiàn)了別人所沒有發(fā)現(xiàn)的事實,才能寫出那種具有高度的時代概括性的作品和人物。可當代的許多作家,是在慣性里寫作,被時代卷著走,他們對一個時代精神氣息的流轉(zhuǎn)并無察覺的敏銳,也無引領(lǐng)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