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第十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文學類)獲獎作品推介(四):《深圳:以小說之名》
更新時間:2018-06-20 來源:廣東文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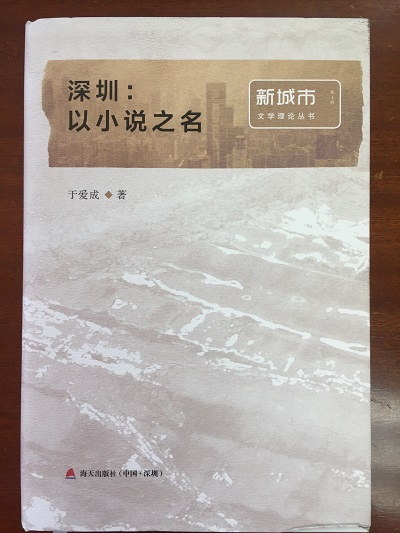
●作者簡介
于愛成,1970年10月生于山東高密,文學博士,研究員,文學創作一級。現任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兼任廣東省作家協會文學評論委員會副主任。迄今已出版《深圳,以小說之名》《新文學與舊傳統》《四重變奏》《狂歡季節》等學術專著,編纂出版《廣東九章》《深圳九章》等合著。曾獲第六屆、第九屆、第十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以及首屆廣東省青年文學獎等獎項。
《深圳:以小說之名》一書,以深圳30多年來小說作品為重點,探討深圳城市文學與城市(空間)、與歷史(時間)的對話關系,如深圳現代性的誘惑與焦慮、深圳夢的追逐與幻滅、深圳城市神話的生成與去魅、文類秩序與象征體系的重組等,力圖建構起研究深圳城市文學(小說)與時間、記憶、欲望和書寫自身的敘事網絡。作品是以都市社會學、新史學的理論資源,以敘事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的方法,對深圳小說進行總體把握,文本細讀,對文學之于深圳城市的建構與想象、深圳文學的主體性建構的過程及其問題,進行了分析。
本書致力于對于城市文學研究的一種新的思考和探索,即由“城市文學”研究向“文學文本與城市文本互文”研究的轉型,由反映論研究轉向注重城市意義表述的研究。?
●名家點評
這本書在對當代中國城市研究進行梳理的同時,對深圳文學的重要作家和作品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與闡釋,為我們勾勒了深圳文學的輪廓。更重要的是,為重講中國故事提供了全新的動力。本書視野開闊,理論扎實,文本分析深入透徹,表現出研究者出色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能力。本書填補了深圳城市文學研究的空白,兼具理論與現實雙重意義。
? ——李楊(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文學理論上,于愛成以深圳小說為例,從深圳文學內部出發,提出新的城市性。全面扎實,厚重,頗具文學史意義,其扎實的文本細讀、沉實中正的批評文字和現實關懷,體現了他是個有人文擔當的批評家。
? ——張燕玲(《南方文壇》主編,著名文學評論家)
這是一部具有明確理論目標的文學批評專著。在這些批評文章里,圍繞著同一理論目標,他提出了自己的對于作品的理論見解,最終完成了自己的理論目標,即建構起深圳的新都市文學話語體系。這樣一種開放性的論述,更完整地保存了文學批評的現場感和有血有肉的質感。同時也充分發揮文學批評在理論中的力度。
——賀紹俊(著名文學評論家)
●精華選讀
?文學與城市:互動、互文、共生的文本
將近40年來,寫深圳的文學作品汗牛充棟,舉不勝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移民作家曾經產生過無法替代的四位現代派作家和一批作品,他們是劉西鴻、譚甫成、石濤和梁大平。《你不可改變我》《小個子馬波利》《大路上的理想者》等作品,是國內文壇較早的現代主義成熟作品,也最早反映了深圳城市化的軌跡和現代性的焦慮。《你不可改變我》獲1986年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然后是深圳文壇的五朵金花,喬雪竹、李蘭妮、彭名燕、黎珍宇、張黎明等,大都以女性的視角,最早呈現了深圳城市化運動中女性意識的自覺。1984年起,表現打工者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的打工文學橫空出世,流風所及,延續至今,涌現了三個代際數百名的打工作家,如張偉明、林堅、安子、郭海鴻、安石榴、戴斌、王十月、衛鴉、郭建勛、謝湘南、陳再見、程鵬、郭金牛等。
拋開著力于表現描繪社會學、政治和經濟學意義上的深圳奇跡的小說家不談,他們從特區成立至今,一直是一股穩定的力量。就純文學意義上談,如果說1985-1989年是第一個黃金時代,早期現代派橫空出世。那么,2000-2004年就是第二個黃金時代,一個龐大的中青年小說家群體開始登上文壇,發出自己各自不同的聲音。然后,將進入了深圳文學的第三個時代。2005年至今,多元、多樣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標志性事件,是70代、80代作家的整體崛起。同時,2000年前后來到深圳或者已在文壇確立地位的作家,無論是南翔、曹征路,還是央歌兒、吳君、盛可以、孫向學、謝宏、丁力、王十月、戴斌等,也完成了各自的涅槃或者說華麗轉身,成為深圳文壇乃至國內文壇的中堅力量,對城市、故鄉、自然、心靈、靈魂等的關注,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2009年,當代文壇享有盛譽的著名作家鄧一光調入深圳,隨即轉入深圳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創作,截至2014年,共寫出30多個作品,出版兩部小說集,作品打破了以往一些小說在敘事上存在的單純的城鄉二元對立的話語體系,真誠地關注和探討城市里的普通人的生存狀態,以及城鄉文化之間的聯系。
文學與城市、小說文本與深圳文本,是一種互生的關系。借用王德威“小說中國”的概念,就引出了“小說深圳”“小說城市”的構思邏輯。深圳-城市-小說之間,因此搭建出來一種互文、互動、共生的關系,互為文本的關系。
城市文學家關注的是與城市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不盡相同的東西。小說家更關心城市的心靈史、城市的象征模式和認知圖式,更關心城市的審美意蘊和城市的如何形式化。小說中的某個具體的意象,比如“陽臺”“臥室”“摩天大樓”,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眼中都是都市建筑空間,但小說家眼中則是心理空間,是巴赫金所說的時空體,是體驗的空間,同時也是修辭空間,最終就是文學空間。一方面是城市生活在文學中獲得了形式,另一方面,文學形式建構了或者說重構了城市生活。尤其是對于后來的讀者而言,認知城市往往要通過文學的建構。因此可以說,城市形象的呈現甚至留存,往往有賴于作家的書寫。如果沒有老舍和張恨水、林語堂,北京的文學記憶乃至歷史記憶要損失大半;沒有新感覺派、茅盾、張愛玲,上海的記憶及其文脈傳承、歷史影響也會大打折扣。所以研究文學中的城市也是揭示一個城市歷史、文化遺存的重要領域。尤其是對城市審美情趣、文化性格以及微觀文化圖景等方面的揭示,只有都市社會史、都市文化史是遠遠不夠的。
隨著歷史和文化的變化,隨著與城市發展密切相關的商業、工業、后工業社會語境的變化,文學要素也在發生著變化。這樣,當文學給予城市以想象性的現實的同時,城市的變化反過來也促進了文學文本的轉變。這正是一種城市與文學之間的共同文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