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biāo)題

標(biāo)題
內(nèi)容
首頁(yè) > 粵讀粵精彩 > 會(huì)員新書架
周朝軍 | 《九月火車》
更新時(shí)間:2018-07-27 來源:廣東作家網(w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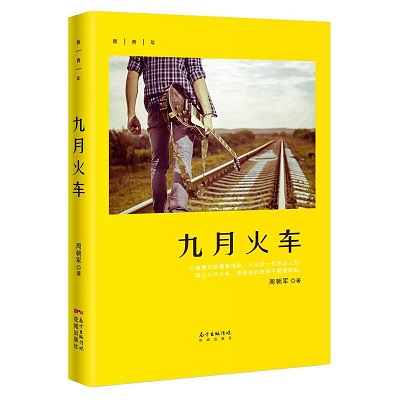
書名:《九月火車》
作者:周朝軍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時(shí)間:2018年7月
簡(jiǎn)介:《九月火車》是一本寫給理想主義者的書。不同于其他年青作者的青春題材作品,雖然書中的幾個(gè)主要人物都是風(fēng)華正茂的青年,都有各自相愛的戀人,故事展開的地點(diǎn)也有相當(dāng)一部分是在大學(xué)校園,但是,“言情”并不是小說的初衷,愛情只是其中無法回避的一部分。這里沒有愛馬仕、LV,沒有旋轉(zhuǎn)餐廳、海天盛筵,沒有“寶馬香車麗人來”。這里有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小青年,有他們的愛與恨,淚與笑,追尋與逃避,脈脈含情與歇斯底里,以及除此之外的一無所有……
周朝軍,曾用筆名黃魚、黃冰、風(fēng)馬等,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魯迅文學(xué)院第34屆高研班學(xué)員,張煒工作室首期學(xué)員,14歲開始發(fā)表作品,作品散見于《作家》、《鐘山》、《北京文學(xué)》、《花城》、《上海文學(xué)》、《山花》、《江南》、《作品》等刊,著有長(zhǎng)篇小說《九月火車》,曾榮獲新加坡晚風(fēng)文學(xué)獎(jiǎng)、豆瓣長(zhǎng)篇小說最佳連載獎(jiǎng)、齊魯文學(xué)年展最佳小說獎(jiǎng)、湖北青年文學(xué)獎(jiǎng)等。2018年4月,經(jīng)《鐘山》雜志社邀請(qǐng),參加第五屆《鐘山》青年作家筆會(huì)。
《九月火車》創(chuàng)作談
這不是一部青春小說,但它確實(shí)記錄了青春的故事。
這部小說完稿于四年前西安市的一棟破樓里。完稿于四年前的這部小說,卻要從十四年以前說起。十四年以前我還是一個(gè)初中的學(xué)生。某個(gè)傍晚,在小鎮(zhèn)的一家舊書店,看到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說,知道了一個(gè)名叫路遙的家伙。隨后兩天,我逃課,躲在一條小河邊的大樹上,沉醉在故事中,忘乎所以。我把自己當(dāng)成了那個(gè)叫孫少平的年輕人,我們一起笑,一起哭。同樣是一個(gè)傍晚,當(dāng)我再三確認(rèn),我確實(shí)讀完了這本書的時(shí)候,我從樹上跳下來,把頭埋在冰冷的河水里。我要忘記整個(gè)故事,然后重新閱讀這本黃土高原上兩對(duì)青年男女的悲歡離合。但是,我不能。我依然清楚地記得書中的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那個(gè)傍晚,一個(gè)兩天里只吃了一頓飯的我,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卻不知說給誰聽。我大吼著,在學(xué)校那條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二十圈,卻依然毫無倦意。夜幕四合,我躺在沒及膝蓋的草坪上,面對(duì)著滿天星斗,放聲大哭。當(dāng)我不久后得知這個(gè)叫路遙的家伙已經(jīng)死去多年的時(shí)候,我悲痛得說不出一句話。那一刻,我決心成為一名作家,寫一部當(dāng)下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
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個(gè)少年,像我一樣,躺在綠油油的草叢里,面對(duì)滿天星斗,放聲哭泣。這些年,我看了很多,也寫了很多,發(fā)表的作品堆起來,也有了厚厚的一沓,偶爾也會(huì)有人把我稱作青年作家。但我始終不曾忘記當(dāng)初的那個(gè)愿望。十年了,我沒有寫過一篇自己喜歡的小說。十年了,我一直在等,等待一個(gè)合適的時(shí)機(jī),開始我筆下的故事。十年了,我仍不知時(shí)機(jī)是否成熟,準(zhǔn)備是否充足。但我知道,我必須寫,哪怕一塌糊涂。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面對(duì)著鏡子里的自己,覺得面目可憎。越不過這道坎,我再也不愿拿起筆,寫下哪怕一個(gè)字。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十年后的那個(gè)傍晚,我打開電腦,將鍵盤再三擦拭。
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十年來我心中流淌著的始終是一個(gè)淳樸而美麗的鄉(xiāng)土故事,心中牽掛著的也始終是孫少平一樣不屈不撓的農(nóng)村青年。但當(dāng)我真正將心中的熱流落實(shí)到文字上的時(shí)候,我才發(fā)現(xiàn),我愛著的青年,不只是孫少平——我愛著的還有剛剛走出校門的自己。所以,我在塑造了周鹿鳴的同時(shí),不得不為他安排一個(gè)雙胞胎哥哥——周劍鳴。也正因?yàn)槿绱耍?jì)劃中的鄉(xiāng)土故事變成了鄉(xiāng)土故事與懷舊青春的夾生飯。
《九月火車》是一本寫給理想主義者的書。不同于其他年青作者的青春題材作品,雖然書中的幾個(gè)主要人物都是風(fēng)華正茂的青年,都有各自相愛的戀人,故事展開的地點(diǎn)也有相當(dāng)一部分是在大學(xué)校園,但是,“言情”并不是小說的初衷,愛情只是其中無法回避的一部分。這里沒有愛馬仕、LV,沒有旋轉(zhuǎn)餐廳、海天盛筵,沒有“寶馬香車麗人來”。這里有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小青年,有他們的愛與恨,淚與笑,追尋與逃避,脈脈含情與歇斯底里,以及除此之外的一無所有……
為凋零的理想作證
——讀周朝軍長(zhǎng)篇小說《九月火車》
管 季
?一
在信仰缺席、道德失準(zhǔn)的當(dāng)下,談?wù)摾硐肷酗@奢侈,如何在理想凋零之后依舊相信且抒寫詩(shī)意人生,發(fā)掘那刺骨的惡下面埋藏的善,就不再是一件簡(jiǎn)單的事。這是處于“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我們無法規(guī)避的真相,也是文學(xué)逐漸邊緣化,逐漸走向下半身、走向多元化、碎片化的根由。當(dāng)我們都淪落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接納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集體幻滅之后,一部由內(nèi)而外都散發(fā)著理想主義光輝的作品的誕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guān)注。
這就是周朝軍的長(zhǎng)篇小說《九月火車》。誠(chéng)然,他是一個(gè)在成人世界中尚顯稚嫩的“90后”,是一個(gè)善用迷宮式的敘事手法來為讀者設(shè)置重重閱讀障礙的年青作家,且在他既往發(fā)表的小說中多半還充斥著古拙的語言、復(fù)雜的修辭和玄奧的隱喻,但在這里,在組成《九月火車》的16萬字里,隱喻消失了,長(zhǎng)得讓人窒息的長(zhǎng)句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近乎自傳的直白敘說。在這直白的敘說中,他將真實(shí)的自己或者理想中的自己一刀刀解剖,然后袒露給讀者。也許這樣的袒露對(duì)于一個(gè)作家來說是非常危險(xiǎn)的,有學(xué)者總結(jié),2010年代之后,青春小說在圖書市場(chǎng)上無以為繼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過多消耗了作者的個(gè)體經(jīng)驗(yàn),但這種經(jīng)驗(yàn)又不能以同等速度在生活與創(chuàng)作中延伸。換言之,假如一個(gè)作家過份仰賴個(gè)體經(jīng)驗(yàn),他終究有一天要面對(duì)寫無可寫的創(chuàng)作窘境。值得慶幸的是,《九月火車》并不是一部傳統(tǒng)意義上的青春小說,我們不會(huì)在閱讀后抱怨自己把一整天的時(shí)間花費(fèi)在了一個(gè)小青年兒的無病呻吟上。毫不諱言,這是一部非常嚴(yán)肅的作品——青春與不嚴(yán)肅沒有共生關(guān)系,從《少年維特之煩惱》到《麥田里的守望者》,從《青春之歌》到《青春萬歲》,這些言說青春與成長(zhǎng)的作品,如今已成為不容置疑的經(jīng)典。在所謂的嚴(yán)肅文學(xué)話語圈里,大家之所以在“青春”面前言辭傲慢,緣于青春的含義與過往已大不相同。如今的青春,首先意味著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無聊青春,意味著自私、無擔(dān)當(dāng),意味著放縱與虛無。早在劉索拉《你別無選擇》的年代,我們已經(jīng)可以窺見“現(xiàn)代生活”對(duì)于年輕人危險(xiǎn)而曖昧的誘惑。同是玩音樂,同是“他媽的”,這些劉索拉們筆下的叛逆生活,在周朝軍這一代作家的筆下已是生活的常態(tài)。但是,無論是劉索拉們還是周朝軍們,“理想”是他們作品中無法回避的。正如《九月火車》前言中所說,“這是一本寫給理想主義者的書”。在“理想”已全面潰敗的當(dāng)下,這種逆“后現(xiàn)代”潮流而上的精神追溯,毫無疑問是需要勇氣的,是嚴(yán)肅的。
二
在《九月火車》的世界里,主人公周劍鳴和周鹿鳴是雙胞胎兄弟,哥哥劍鳴是魯南師大哲學(xué)系學(xué)生,弟弟鹿鳴則是水縣瓷廠裝卸工。意氣風(fēng)發(fā)的大學(xué)生活剛開始,劍鳴就遇到了幾個(gè)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和同樣喜歡音樂的蘇野、佴志全、關(guān)琳等人組成了一個(gè)“藍(lán)蓮花樂隊(duì)”,成為了魯南師大的風(fēng)云人物。在一次學(xué)生集體事件中,“藍(lán)蓮花樂隊(duì)”的成員在校長(zhǎng)頭上澆了紅墨水。高傲的劍鳴不肯道歉,于是輔導(dǎo)員找來劍鳴的雙胞胎弟弟鹿鳴頂替他向校長(zhǎng)道歉。真相被劍鳴知道之后,他負(fù)氣遠(yuǎn)走西安。再看鹿鳴這邊,盡管干著裝卸工的活,卻一直堅(jiān)持小說創(chuàng)作,并與師大女生喬雅惺惺相惜。在工廠里,他受人排擠,失去工作,繼而先后成為小學(xué)老師、郵差和“破爛王”。正當(dāng)兩兄弟踟躕在命運(yùn)的十字路口,汶川地震突然降臨。喬雅親赴救援現(xiàn)場(chǎng),在余震中失去了生命,劍鳴也在地震中成長(zhǎng),回歸了學(xué)校。畢業(yè)之后,劍鳴與女友關(guān)琳浪跡天涯(當(dāng)然周劍鳴也可能是留下女友自己遠(yuǎn)走高飛,作者一貫喜歡設(shè)置模糊的結(jié)局),而鹿鳴實(shí)現(xiàn)了自己的理想,成為了作家,同時(shí)也失去了愛情。
在16萬字的篇幅里,小說設(shè)置了兩條主線——一條以劍鳴的校園生活為主,一條以鹿鳴的鄉(xiāng)村生活為主,兩條線鋪就了一個(gè)巨大的敘事框架。暫且不論作者是否有駕馭這么大框架的能力,但他的格局和野心是顯而易見的——他要把它寫成一部當(dāng)代版的《平凡的世界》。小說向我們展示了青春文學(xué)中不多見的鄉(xiāng)村少年生活,并真實(shí)而犀利地指出了一系列社會(huì)問題。因此,這部小說既不同于《你別無選擇》的現(xiàn)代派風(fēng)格,也不同于常見的校園小說,甚至極大地淡化了言情成分。它立足于現(xiàn)實(shí)的視角,在真實(shí)中激蕩著理想,在受難中反思著成長(zhǎng)。隨著開篇的油滑和打趣,逐步轉(zhuǎn)化為結(jié)尾的沉重,主人公的青春也經(jīng)受了一次殘酷洗禮。
殘酷青春,并不是一個(gè)陌生的詞匯,在文學(xué)中往往伴隨著對(duì)80后一代成長(zhǎng)的解讀,也伴隨著性、暴力和邊緣文化。春樹早在發(fā)表《北京娃娃》之時(shí),就為人們展現(xiàn)了這種“朋克”式的青春,并建立起人們對(duì)于殘酷青春的固定印象。她顛倒了“殘酷”的定義,把那種無所事事的墮落和無休止的失戀稱為殘酷,并不厭其煩地展現(xiàn)音樂、酒精、性、暴力等等迷醉的狂歡,并以此作為生活的真相。在這一點(diǎn)上,周朝軍顯然比同齡人認(rèn)識(shí)更為深刻。雖然《九月火車》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搖滾,甚至部分情節(jié)還要依靠音樂來發(fā)酵——如周劍鳴通過借吉他認(rèn)識(shí)了女友關(guān)琳,在賣唱被城管驅(qū)趕的過程中認(rèn)識(shí)了蘇野和佴志全,在西安通過賣唱得到了生活費(fèi)和另一位好心大姐的照顧——故事開始于音樂,也成全于音樂,但一把吉他,支撐的是周劍鳴純粹的理想和信念,是他對(duì)人生的熱望。假如單純與春樹筆下的朋克少女比較,搖滾少年周劍鳴顯然更為底層的。在春樹筆下,樂隊(duì)不是用來掙錢的,而是主人公的感情寄托,作為北京原住民的她根本不用為生計(jì)發(fā)愁,她毅然輟學(xué)奔赴樂隊(duì),是因?yàn)樗胂竽苡袠逢?duì)成員的擁抱與傾聽,能有一種純粹而激烈的感情;而在《九月火車》中,周劍鳴賣唱糊口,掙扎在自尊與生存中。他背起吉他走天涯,但這個(gè)天涯是一個(gè)沒有安穩(wěn)住所、沒有華服美食的天涯,是維持最低限度生存的流浪。比起那種純粹的叛逆和理想,周劍鳴的音樂夢(mèng)想顯然更為現(xiàn)實(shí),也更為卑微,正因?yàn)槿绱爽F(xiàn)實(shí)和卑微,才代表了理想的高度。沒有現(xiàn)實(shí)作為對(duì)照的理想是無根之理想,而從金錢浸潤(rùn)中蓬勃而出的理想,則更具有力度。因此,與其說周朝軍塑造了幾個(gè)理想主義者,不如說他其實(shí)深刻理解了現(xiàn)實(shí)的殘酷。從來沒有一種生活是完美的,這是《九月火車》著力表達(dá)的東西。比如,在結(jié)局中,同樣立志于音樂道路的佴志全,在北京,與女友唯佳只能租住在陰冷的小平房里奢望明天。小說以春秋筆法寫到唯佳為了男友的理想犧牲了色相,其中過程作者隱而不說,但越是掩飾,就越能感受到現(xiàn)實(shí)的殘酷。好在周朝軍給了我們一個(gè)溫暖的結(jié)局中——佴志全和唯佳有情人終成眷屬——在帝都生活的風(fēng)浪中,他們還能走多遠(yuǎn),沒有人知道。
當(dāng)然,這還遠(yuǎn)不能代表《九月火車》所能達(dá)到的的高度,書寫完殘酷青春,周朝軍從年青人的命運(yùn)中跳脫出來,繼續(xù)關(guān)注更為廣闊的現(xiàn)實(shí)。小說中描寫到三次學(xué)生事件,第一次起因于學(xué)生宿舍緊缺,校方把學(xué)生們安排到離學(xué)校很遠(yuǎn)的、條件很差的宿舍中。學(xué)生上學(xué)路上不安全,于是周劍鳴就給校長(zhǎng)拍了桌子,換來的是五門課不及格,繼而引發(fā)學(xué)生集體示威;第二次是學(xué)校的小賣部狗仗人勢(shì),打傷學(xué)生,事件經(jīng)網(wǎng)絡(luò)發(fā)酵,以周劍鳴為首的“藍(lán)蓮花樂隊(duì)”直接朝校長(zhǎng)頭上潑了墨,這次周劍鳴得到的是“開除”;第三次集體事件從校園走向了社會(huì),還涉外,周劍鳴的室友胖三在日本公司實(shí)習(xí)期間,不僅受盡折磨,還被克扣工資,辭職不成反被打到失聰。這一次,討說法的學(xué)生得到了校長(zhǎng)的支持,大家合力為胖三討回了公道,校長(zhǎng)與學(xué)生達(dá)成和解,并重新樹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這些看似戲劇化實(shí)際極現(xiàn)實(shí)的學(xué)生事件,在不動(dòng)聲色中觸及了某些規(guī)則的邊緣。在以往的青春小說中,還沒有一部作品敢如此直白地把“示威”這樣一個(gè)集體行為寫得如此酐暢淋漓理直氣壯——尤其是在觸及到政治層面時(shí)。在今天,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仍是禁忌,但周朝軍很好地把握了這個(gè)度。幾次群體事件,一方面完美塑造了周劍鳴的熱血青年形象,另一方面又向讀者展示了作者心中理想的生活圖景。周朝軍筆下的青年非但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墮落,反而渾身都散發(fā)著理想主義精神。但現(xiàn)實(shí)生活過于平凡,容納理想的方式僅僅只是向校長(zhǎng)示威,年輕人的生活也僅僅局限于大學(xué)校園及周邊。為了讓筆下的人物掙脫校園的束縛,周朝軍把汶川地震寫進(jìn)了小說。周劍鳴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能在某種大的歷史場(chǎng)景去表達(dá)自己的理想,甚至他們不知自己在歷史中處于何種地位。從小鎮(zhèn)來到大學(xué)校園,仿佛就是一個(gè)普通人能觸及到的最寬廣的道路了。但地震讓年青人有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激昂和悲愴感,他們終于能在一個(gè)時(shí)代性的事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周劍鳴的腦海中有一部屬于自己的史詩(shī),他把所有不相關(guān)的苦難變成自己的重負(fù),意欲與整個(gè)世界決戰(zhàn),從而獲得心目中的崇高感。這樣的反叛,在現(xiàn)實(shí)主義者眼中自然是徒勞的,但卻是古往今來的人們得以保持精神獨(dú)立的一大法寶。
三
《九月火車》中對(duì)鄉(xiāng)村生活的描寫,調(diào)和了全書過于激昂的理想主義情結(jié)。周鹿鳴作為雙胞胎哥哥周劍鳴的另一面,低調(diào)而堅(jiān)強(qiáng)。他將上大學(xué)的機(jī)會(huì)讓給了哥哥,自己成為一名裝卸工,出賣苦力,但從未停止思考,他將生產(chǎn)的經(jīng)驗(yàn)寫成論文,獲得廠領(lǐng)導(dǎo)的賞識(shí),但現(xiàn)實(shí)并沒有眷顧這個(gè)喜歡寫作的年輕人,他在拒絕了廠領(lǐng)導(dǎo)的離婚女兒的示愛之后,遭到了眾人的排擠。失去工作之后,他與小姨水芬也被動(dòng)地卷入了鎮(zhèn)上錢、李兩家人的官場(chǎng)爭(zhēng)斗中,鹿鳴的職業(yè)生涯也因此一波三折。在困境中,支撐他的是女友喬雅的賞識(shí)和鼓勵(lì),但在汶川地震數(shù)月后的一次余震中,喬雅也不幸遇難。周鹿鳴這一形象,即使是在新世紀(jì)的鄉(xiāng)土小說中,也是不多見的,我們需要追溯到路遙的黃土高坡,才能理解周鹿鳴的精神依附。假如說周劍鳴的理想是在城市的繁華中保留一個(gè)心靈的出口,那么周鹿鳴則是對(duì)哺育他的大地報(bào)以深情。盡管在小說的最后周鹿鳴成為了當(dāng)?shù)赜忻淖骷遥谒某砷L(zhǎng)歷程中,成名只是一個(gè)奮斗的附屬品,奮斗本身即是目的。周鹿鳴是一個(gè)心中沒有丑惡、沒有自卑和不甘,對(duì)一切苦難泰然視之的底層人物形象。無論生活的面目如何猙獰,周鹿鳴始終沒有迷失自我。在惡的環(huán)境中提煉出來的善意,總是具有更為豐富的層次,也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yàn):原來90后作家也能寫好底層,寫好鄉(xiāng)村。鄉(xiāng)村有靈魂,這種靈魂不僅讓50后一代戀戀不舍,也讓90后作家周朝軍把握住了即將逝去的鄉(xiāng)村給人帶來的最后一絲精神慰藉。
在對(duì)鄉(xiāng)村人物的描寫中,周朝軍給當(dāng)代文學(xué)貢獻(xiàn)了兩個(gè)極為典型的人物形象:一個(gè)是水芬小姨,一個(gè)是大舅。周鹿鳴的性格受水芬的影響,她陪伴鹿鳴長(zhǎng)大,相當(dāng)于他的母親。但這個(gè)美麗淳樸的女人,背負(fù)著“克夫”的詛咒,兩任丈夫都相繼暴斃,這盡管是發(fā)生在現(xiàn)代鄉(xiāng)村,也仍舊是極為轟動(dòng)的事件。不同于其它描寫女性命運(yùn)或者批判鄉(xiāng)村落后觀念的作品,《九月火車》并不直接抒發(fā)恨意,也沒有設(shè)置直接的批判對(duì)象。首先,水芬的兩任丈夫死亡是小概率事件,純屬意外;其次,水芬的不幸并不是由他人導(dǎo)致的。既沒有外界的加害者,也沒有主觀的恨意,水芬的悲劇因而上升至某種哲學(xué)或者宗教層面的——眾生皆苦。人生要面對(duì)無盡的偶然性,人在這種時(shí)刻充滿偶然的世界中,活得像一株堅(jiān)韌的植物,盡管被雨水沖刷,被風(fēng)吹倒,卻用根基牢牢抓緊大地。這讓我們想起余華的《活著》,面對(duì)突如其來的死亡,人除了接受命運(yùn)別無他法;也讓我們想起蕭紅的《生死場(chǎng)》,人腐爛的肉身浸滿了蛆,卻也必須瞪大那枯槁的眼睛。這種掙扎的生命,受難的美學(xué),就是小說想要表達(dá)的鄉(xiāng)村之魂。同樣,鹿鳴的大舅也是一個(gè)“有故事的人”。他年輕的時(shí)候,因?yàn)槭恰暗刂髦蟆保c相愛的人不能相守。姑娘嫁給了別人,再也沒回過柳溪鎮(zhèn)。五十多年以后,她回來了,終生未婚的大舅一個(gè)人躺在屋子里,嚎啕大哭。盡管提到大舅的篇幅非常少,仍可窺見作者對(duì)于上一代人命運(yùn)的深切思考。小說中另一個(gè)著墨不多的人物“表叔”——表叔年輕的時(shí)候成績(jī)非常好,卻被當(dāng)權(quán)者掉包了高考試卷,而其不能反抗、不能言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身上的“地主成分”。讓我驚訝的人是,歷史的傷痕,仍在作者這個(gè)90后的記憶里延續(xù)著;他記憶著,言說著,不讓若干年之后的下一代忘記。這種傳承,顯示出一個(gè)作家最基本的責(zé)任感,也讓小說有了更為沉重的社會(huì)意義。而大舅這個(gè)人物形象,寥寥幾筆足卻刻畫出了他的樸實(shí)和深情。身為弱者,在人生被摧殘得一無所有之后,仍能忠于自我,忠于感情。這既是鄉(xiāng)村之魂,也是作為一個(gè)人最真實(shí)、最絢爛的生命綻放。
在苦難中抵達(dá)一種詩(shī)意的存在之境,是小說通過人物命運(yùn)給讀者的深刻啟示。借由周鹿鳴、水芬、大舅這些人物,周朝軍得以在小說中建立一種“新鄉(xiāng)村”形象。這里,既沒有夸張的悲情,也沒有尖銳的批判,有的只是淡淡的落寞,和對(duì)存在意義的追索。不管外界如何卑瑣,不管生命本身多么殘酷,所有人都有著某種清醒的自覺,不輕易降低自己對(duì)于理想的標(biāo)準(zhǔn)。這比單純?yōu)榱伺卸鴮懙讓樱蛘邽榱送槎鵀榈讓影l(fā)聲,更加具有現(xiàn)實(shí)的意義。畢竟,現(xiàn)實(shí)中不是只有追求寶馬LV的孩子,也不是所有人都談著不負(fù)責(zé)任的戀愛,還有一種如周鹿鳴這樣的人,真實(shí)存在著。這些善良的人,需要被正視,被銘記。
四
通過小鎮(zhèn)柳溪,周朝軍寫出了一個(gè)作家對(duì)于故鄉(xiāng)的愛與悲憫。固守著理想主義的周劍鳴、周鹿鳴身上,那些純凈而堅(jiān)韌的品質(zhì),并不完全是一種人為的拔高,而是作者對(duì)于時(shí)代崇高精神的注解與希冀。這種希冀的根源,正是出于對(duì)愛的信心。作者可以不愛這個(gè)社會(huì),不愛任何其他人,但他愛故鄉(xiāng),愛故鄉(xiāng)曾經(jīng)的少年。這讓我們想到雷平陽(yáng)的那首《親人》:
我只愛我寄宿的云南,因?yàn)槠渌?/span>
我都不愛;我只愛云南的昭通市
因?yàn)槠渌形叶疾粣郏晃抑粣壅淹ㄊ械耐脸青l(xiāng)
因?yàn)槠渌l(xiāng)我都不愛……
我的愛狹隘、偏執(zhí),像針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
我會(huì)只愛我的親人——這逐漸縮小的過程
耗盡了我的青春和悲憫
這逐漸縮小的范圍,也是周朝軍理想的載體。他所表達(dá)的理想主義并不是空泛、虛無的理想,而是面對(duì)親人、朋友和過去的自己所滋生出來的那種深切的同情心,是每個(gè)人身上曾有過的真實(shí)的、可以觸摸的夢(mèng)——比如說大舅和水芬的愛情,比如說周劍鳴的音樂夢(mèng)想和鹿鳴的寫作夢(mèng)想。這種理想和同情,以及由此而來的對(duì)于故鄉(xiāng)人物的美化,構(gòu)成了小說基本的審美基調(diào),因而帶有著本雅明所說的“靈光”:時(shí)空的奇異糾纏,遙遠(yuǎn)之物的獨(dú)一顯現(xiàn),雖遠(yuǎn),猶如近在眼前。鄉(xiāng)村的靈光帶著夢(mèng)幻和唯美,和濃厚的烏托邦情結(jié),讓每一個(gè)遠(yuǎn)在天邊的游子,一想起故鄉(xiāng)就能感受到那種微妙的心痛和深沉的情感。在當(dāng)代作家的筆下,其實(shí)并不乏這種帶有神性的靈光,事實(shí)上,幾乎每一個(gè)描寫鄉(xiāng)土的作家都會(huì)視故鄉(xiāng)為某種精神信仰,如沈從文,如汪曾祺,如莫言和賈平凹。周朝軍在小說中不自覺地寫到渡口:
初次來水縣的人,一過河,就有了如夢(mèng)似幻的感覺。青山綠水,竹筏子,擺渡人,對(duì)于見慣了燈紅酒綠的人們,總有一種隔世之感,仿佛自己不是置身全球化時(shí)代的中國(guó)東部鄉(xiāng)村,而是到了某個(gè)上世紀(jì)初的南方小鎮(zhèn)。
但很快話鋒一轉(zhuǎn),略帶戲謔地寫道:
待見了鎮(zhèn)里人,騎著電動(dòng)車、摩托車,開著小轎車走街串巷,或者拿著手機(jī)說著與河對(duì)岸并無二致的本地方言,才恍然悟到自己還是在原來的世界,心頭詫異著,人口繁密的魯南,偏偏就還藏著這樣一個(gè)世外桃源一樣的地方呢!
桃源還是那個(gè)桃源,但卻不是沈從文筆下那個(gè)人性美好、不沾世俗煙火氣的邊城。在這里也能看出周朝軍這一代90后作家筆下的鄉(xiāng)村,天然就具有了復(fù)雜的特征。他眼中的景色仍是美好的,親人是善良的,但他也清楚知道事實(shí)上的鄉(xiāng)村遠(yuǎn)不止于此。現(xiàn)代化這條必由之路,讓鄉(xiāng)村的神性與其世俗性逐漸剝離,“靈光”變成某種尷尬的存在,甚至逐漸消失了。與之一同消失的,還有那種對(duì)烏托邦的想象。?
顯然,在《九月火車》中,作者建立起了一種復(fù)雜的、悖謬的對(duì)立機(jī)制。他的理想主義的范圍縮小至身邊熟悉的人,而這之外的幾乎所有人——家族勢(shì)力、工廠領(lǐng)導(dǎo)、工人、有后臺(tái)的小賣部老板,無一例外都是加害者。鄉(xiāng)村中的人情,也并沒有想象中那樣曠達(dá),正如小說中所說,平時(shí)那些憨厚老實(shí)的工人們,因?yàn)閺S長(zhǎng)的命令,很快孤立了周鹿鳴:
在自身利益面前,這些農(nóng)閑時(shí)強(qiáng)健的裝卸工、農(nóng)忙時(shí)粗糲的莊稼漢子,身體內(nèi)隱匿的自私的小農(nóng)意識(shí),很快就抬頭了。
被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所染指的鄉(xiāng)村,不僅有了手機(jī)、電動(dòng)車、小汽車,也獲得了與資本息息相關(guān)的逐利特性。鄉(xiāng)村也得以實(shí)現(xiàn)“祛魅”的過程,向城市逐漸靠攏,其理想化的淳樸人性被世俗擠壓,逐步走向了歷史邊緣。描述這種變化是有意義的,對(duì)周朝軍這樣一個(gè)年輕作家來說,體會(huì)這種變化,以及理想的消逝所帶來的虛無感,是一種必要的歷練。鄉(xiāng)村少年走向城市,所經(jīng)歷的種種平凡、無趣、無序的人生,是作者借以觀照整個(gè)人生的立足點(diǎn)。隨著肉身的死亡,以及那些可見的悲劇,一個(gè)人在這個(g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真正凸顯了出來,那是一種哲學(xué)意味上的孤獨(dú),是必要的順應(yīng),是無為的反抗。當(dāng)然,作品的意義,也包括這種反抗的徒勞。
關(guān)于鄉(xiāng)村,關(guān)于烏托邦,關(guān)于現(xiàn)實(shí),關(guān)于反抗,關(guān)于理想——每個(gè)人心中都有,但重要的是,每個(gè)人都認(rèn)為自己心目中的現(xiàn)實(shí)才是現(xiàn)實(shí)。詹姆斯·伍德說過這樣一句話:詩(shī)人和小說家循環(huán)往復(fù)地攻擊某種現(xiàn)實(shí)主義,為的是宣揚(yáng)他們自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在表達(dá)的技巧上,文學(xué)作品總是可以分出高下;但在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和理想的理解,始終是沒有一個(gè)固定標(biāo)準(zhǔn)的,而且很遺憾,很多人其實(shí)并不能互相理解。正如我們不止一次地抨擊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青春文學(xué),或者那些用自身經(jīng)歷所凝聚成的抒情文字,認(rèn)為這是膚淺的理想,墮落的生活——我們又何嘗不是在表達(dá)自己的理想呢?
文學(xué)本身,作為一種深刻的理想主義,必然要由理想來呼應(yīng)。不諱談理想,是對(duì)一部好作品的內(nèi)在要求,這一點(diǎn),《九月火車》做到了——這種真實(shí)的自我敞開,足以令人印象深刻。其對(duì)于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格局的把握,對(duì)于年輕人的精神困惑的描寫,包括人在災(zāi)難面前的自省,都已經(jīng)具有了某種嚴(yán)肅的思想性。當(dāng)我們默認(rèn)了理想的幻滅,并以談?wù)摾硐霝閻u的時(shí)候,也許更需要有人為信念、為自由、為鄉(xiāng)村烏托邦和純潔的愛情作證,為破敗的理想作證,并倔強(qiáng)而堅(jiān)韌地走下去。
作者簡(jiǎn)介:管季,女,80后,湖南人。中山大學(xué)中文系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博士生。
《九月火車》開向何處——
王祥夫、李浩、管季對(duì)談周朝軍
王祥夫:朝軍,首先恭喜你的長(zhǎng)篇小說順利發(fā)表,這真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坦白地講,初讀這部作品,我曾一度認(rèn)為這是一部快餐式的青春小說,尤其是從前言部分了解到,小說完稿于2013年,當(dāng)時(shí)你應(yīng)該剛剛大學(xué)畢業(yè)。如果不是在此前已經(jīng)看到過你的一些中短篇作品,對(duì)你的寫作已經(jīng)有了不錯(cuò)的印象,我很可能會(huì)武斷地放棄這樣一部精彩的小說。幸運(yùn)的是,我用一整天讀完了它,少有的一次愉快的閱讀體驗(yàn),很棒。我很好奇,你在完成這部作品之后,有沒有因?yàn)槟挲g和題材的原因遇到過一些誤讀,或者因此給出版和發(fā)表帶來了一些困擾?
周朝軍:祥夫老師一開口就戳中要害。這部小說確實(shí)完稿已經(jīng)有四個(gè)年頭了,與我的中短篇小說相比,《九月火車》的確命運(yùn)坎坷。長(zhǎng)篇難發(fā)表,年青作者的長(zhǎng)篇更難發(fā)表,但這不是問題的關(guān)鍵,更重要的還是題材不討巧,好像一沾上大學(xué)校園,尤其是當(dāng)下的大學(xué)校園,就不嚴(yán)肅了,不純文學(xué)了。我能想象得到,二十年以后,甚至只需要十年以后,大家再看《九月火車》就會(huì)不一樣,因?yàn)橛辛四甏校瑲v史感。有了年代感,歷史感,直觀感受上就厚重了。但現(xiàn)實(shí)情況是,我在2013年就交出了這部作品,此后四年的時(shí)間里,我先后向四家雜志社投遞了這部作品,與我預(yù)想的一樣,稿子很快就進(jìn)了他們電腦的回收站。我這么說,不是批評(píng)各位編輯,畢竟我在寫作這個(gè)行當(dāng)里還是新手,我也不是一個(gè)多么優(yōu)秀的作者。
在雜志社這邊碰了壁之后,退而求其次,我開始嘗試著在網(wǎng)上連載,以前沒這么干過。出乎預(yù)料,在豆瓣閱讀頻道連載一個(gè)月,就拿了他們一個(gè)最佳連載獎(jiǎng),幾乎是同一時(shí)間,十幾家圖書公司通過豆瓣給我發(fā)來了郵件,表示想出版這部作品。我對(duì)圖書市場(chǎng)不太了解,隨意挑了其中一家,簽了合同,然后很快就拿到了預(yù)付款。前面的環(huán)節(jié)太順利,后面的事情我完全沒想到。直到合同到期,這家圖書公司也沒能拿到《九月火車》的書號(hào),他們轉(zhuǎn)述說,出版部門給的答復(fù)是三觀不正。我不服氣,又從此前發(fā)來郵件的圖書公司里選了兩家。于是讓我更想不到的事發(fā)生了,和第一家公司如出一轍,我先后輕松地拿到了他們的預(yù)付款,也先后收到了他們類似“三觀不正”的答復(fù)。事不過三,我開始不自信了,開始自我懷疑了,直到收到《時(shí)代文學(xué)》這邊擬用的通知。
壓抑了四年之后,終于等到了曙光。如您所說,我真是高興壞了,收到消息的當(dāng)天晚上,我一個(gè)人,自斟自飲,狠狠地喝了一頓酒。無巧不成書,收到《時(shí)代文學(xué)》通知的第二天,此前簽約的三家圖書公司中的兩家,在相差不到半個(gè)小時(shí)的時(shí)間里,一前一后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說書號(hào)已經(jīng)不成問題,愿意馬上續(xù)簽合同。但此時(shí)我對(duì)出版已不再迫切,還是讓《九月火車》先開回山東老家,開進(jìn)2017年冬天,開進(jìn)《時(shí)代文學(xué)》吧。
王祥夫:你是如何想到要?jiǎng)?chuàng)作這樣一部作品的,醞釀了多久?另外,以我對(duì)你的了解,《九月火車》這部小說帶有很強(qiáng)的自傳色彩,很多人物應(yīng)該都是有原型的吧?
周朝軍:關(guān)于創(chuàng)作,我有一個(gè)觀點(diǎn),我想很多人都能認(rèn)同,您也能認(rèn)同:不管是大作家還是小作者,不管他一生中的創(chuàng)作是何等的豐富,他的審美趣味、文學(xué)觀都會(huì)受到他成年以前的經(jīng)歷和閱讀的深刻影響,而審美趣味、文學(xué)觀會(huì)不自覺地滲透到一個(gè)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并將或大或小地影響他一輩子的創(chuàng)作。對(duì)我影響最大的一部書是《平凡的世界》。承認(rèn)《平凡的世界》是影響我最大的一部書,一定會(huì)讓某些人失望。如果我搬出一部外國(guó)作品,尤其是那些在國(guó)外也十分冷門、十分小眾、十分前衛(wèi)的作品,在眾人面前,我立馬顯得學(xué)問淵博高深莫測(cè)起來。當(dāng)我說出一部非洲東部地區(qū)某個(gè)鳥不拉屎的地方、某個(gè)八流作家作品的時(shí)候,我相信,即便是我的同行,也會(huì)立馬對(duì)我另眼相看,我甚至能夠想象到他們假裝也看過這部作品時(shí)那心虛的表情。盡管《平凡的世界》發(fā)行量無與倫比,影響過千千萬萬的人,但在文學(xué)界,它得到的評(píng)價(jià)和它的影響力卻極不匹配,說的直接點(diǎn),《平凡的世界》在文學(xué)界評(píng)價(jià)不高。然而恰恰是這部作品,使我走向了寫作的道路,并深深地影響了我23歲以前的寫作。為了向路遙致敬,也為了盡早放下路遙對(duì)自己的影響,我寫了這部我自己心中的《平凡的世界》——《九月火車》,算是向以前的自己告別,向路遙告別。有意思的是,在創(chuàng)作《九月火車》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shí)到,我一直以來可能高估了路遙施加給自己的影響,或者說,我再一點(diǎn)點(diǎn)擺脫路遙的影響。這正是我想要的——一個(gè)有野心的作者是不該站在前人的背影里寫作的。所以,《九月火車》雖被讀者謬贊為當(dāng)下版《平凡的世界》,但我還是寫出了自己的風(fēng)格,《九月火車》就是《九月火車》。
寫作《九月火車》我大概只用了40天,但是細(xì)究起來,我足足醞釀了6年。一開始縈繞在我腦海中的只是一些模糊的人物形象,或者一些碎片化的情節(jié),直到2013年春天,這些人物,這些碎片化的情節(jié),才一點(diǎn)點(diǎn)在我的word文檔里串起來。
說到小說的原型問題,我坦白從寬,《九月火車》基本算是一部半自傳體小說。男主人公周鹿鳴、周劍鳴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我性格的不同側(cè)面,現(xiàn)實(shí)中的我和他們有著一樣的家世。我兄弟姊妹6人,出生六個(gè)月就被父母過繼給了我單身的大舅。小說中大舅的形象完全照搬現(xiàn)實(shí),一絲一毫的虛構(gòu)都沒有,連名字都一樣。還有像小說中的水芬小姨、佴志全、胖三等人物都確有其人。
王祥夫:我注意到一個(gè)非常經(jīng)典的女性形象——水芬小姨。與你小說中的其他女性形象相比,水芬小姨這個(gè)角色顯然更飽滿,更符合我對(duì)女性的審美期待。可否簡(jiǎn)單的談一下這個(gè)人物。
周朝軍:我剛才有提到,水芬小姨這個(gè)人物現(xiàn)實(shí)中卻有原型,但是考慮到當(dāng)事人的隱私問題,這里我不便多說。但有一點(diǎn)可以談,就是水芬小姨這個(gè)人物確實(shí)代表了我對(duì)鄉(xiāng)村女性的美好想象,她是我心中真、善、美的化身,但很不幸,現(xiàn)實(shí)中的原型比小說中的水芬小姨命運(yùn)還要悲慘,她三次喪夫,至今孑身一人。
王祥夫:如果我們單從題材出發(fā),把《九月火車》劃歸青春小說,那么你覺得,相比于圖書市場(chǎng)上其他的青春小說,《九月火車》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周朝軍:我個(gè)人覺得,最大的不同還是在它的整體氣質(zhì)上。青春小說也好,網(wǎng)絡(luò)小說也罷,他們與嚴(yán)肅文學(xué)產(chǎn)生差異的根由,不是傳播媒介,不是題材,不是受眾,而是作者本人的文學(xué)觀決定了作品的定位。我是在嚴(yán)肅文學(xué)的浸潤(rùn)下走向?qū)懽鞯模詿o論我書寫何種題材,我的寫作初衷都是嚴(yán)肅的,與那些帶有快餐性質(zhì)的青春小說還是有著本質(zhì)不同的。
另外我還是想強(qiáng)調(diào)一下,一部作品嚴(yán)肅與否,和題材本身沒必然關(guān)系,如果說書寫青春就意味著不嚴(yán)肅,那么像《霧都孤兒》《哈克費(fèi)恩歷險(xiǎn)記》《城南舊事》等兒童視角的作品,以及像張煒老師的《尋找魚王》這樣的兒童文學(xué)作品又該如何劃分?
李浩:還是應(yīng)該先恭喜你,朝軍。我是在九月的火車上讀完《九月火車》的,老實(shí)說,因?yàn)榇饲皩?duì)你的中短篇作品已有一個(gè)大體的把握,所以這次看到《九月火車》時(shí)候,我還是有些驚訝的。好像一個(gè)拍慣了動(dòng)作大片的導(dǎo)演,突然放棄了各種特效老老實(shí)實(shí)一招一式地真打了,讓我看到了你內(nèi)心真實(shí)的一面,看到了你這一代人的擔(dān)當(dāng)。另外。我注意到《九月火車》的電子版在網(wǎng)上很受歡迎,據(jù)說賣出了8萬多冊(cè),這個(gè)數(shù)字如果放到圖書市場(chǎng)上,算是相當(dāng)暢銷了。你連載的網(wǎng)站在宣傳這部作品的時(shí)候,給了這樣一個(gè)廣告語,“當(dāng)下版《平凡的世界》,小城青年的青春挽歌”。的確如此,小說中周鹿鳴這個(gè)人物,他身上那種樸實(shí),那種堅(jiān)強(qiáng),很難不讓人聯(lián)想到路遙筆下的孫少平,給大家談一談路遙對(duì)你影響吧。
周朝軍:浩哥,您和祥夫老師真是默契,您兩位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路遙對(duì)我的影響,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其實(shí)我在小說前言中有過清晰地表述,其中關(guān)于路遙的那兩三個(gè)段落,我至今能夠背誦,如果您不嫌棄,我背給您聽:
十四年以前。
十四年以前我還是一個(gè)初中的學(xué)生。某個(gè)傍晚,在小鎮(zhèn)的一家舊書店,看到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說,知道了一個(gè)名叫路遙的家伙。隨后兩天,我逃課,躲在一條小河邊的大樹上,沉醉在故事中,忘乎所以。我把自己當(dāng)成了那個(gè)叫孫少平的年輕人,我們一起笑,一起哭。同樣是一個(gè)傍晚,當(dāng)我再三確認(rèn),我確實(shí)讀完了這本書的時(shí)候,我從樹上跳下來,把頭埋在冰冷的河水里。我要忘記整個(gè)故事,然后重新閱讀這本黃土高原上兩對(duì)青年男女的悲歡離合。 但是,我不能。
十年后,我在西安,我依然不能,我依然清楚地記得書中的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那個(gè)傍晚,一個(gè)兩天里只吃了一頓飯的我,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卻不知說給誰聽。我大吼著,在學(xué)校那條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二十圈,卻依然毫無倦意。夜幕四合,我躺在沒及膝蓋的草坪上,面對(duì)著滿天星斗,放聲大哭。當(dāng)我不久后得知這個(gè)叫路遙的家伙已經(jīng)死去多年的時(shí)候,我悲痛得說不出一句話。那一刻,我決心成為一名作家,寫一部當(dāng)代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個(gè)少年,像我一樣,躺在綠油油的草叢里,面對(duì)滿天星斗,放聲哭泣。這些年,我看了很多,也寫了很多,發(fā)表的作品堆起來,也有了厚厚的一沓,偶爾也會(huì)有人把我稱作青年作家。但我始終不曾忘記當(dāng)初的那個(gè)愿望。十年了,我沒有寫過一篇自己喜歡的小說。十年了,我一直在等,等待一個(gè)合適的時(shí)機(jī),開始我筆下的故事。十年了,我仍不知時(shí)機(jī)是否成熟,準(zhǔn)備是否充足。但我知道,我必須寫,哪怕一塌糊涂。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面對(duì)著鏡子里的自己,覺得面目可憎。越不過這道坎,我再也不愿拿起筆,寫下哪怕一個(gè)字。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十年后的那個(gè)傍晚,我打開電腦,將鍵盤再三擦拭。
李浩:小說中有一個(gè)“賈先生”,我注意到這是他在你的小說中第三次出現(xiàn)了。前兩次是在《山東毛驢與墨西哥舞娘》和《沂州筆記》中。這個(gè)人是確有其人,還是你虛構(gòu)的一個(gè)古典俠士形象?他是否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你心目中的古典主義理想人格?
周朝軍:感謝浩哥提了這么一個(gè)容易回答的問題,我的回答很簡(jiǎn)單: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心目中的古典主義理想人格。
李浩:讀《九月火車》,我能感覺到你是非常喜歡音樂的。談一下音樂對(duì)你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哪些影響。
周朝軍:這個(gè)問題很有意思,我雖然沒和別的寫作者交流過這個(gè)問題,但我很肯定,一定有很多同行像我一樣,他們?cè)趧?chuàng)作的時(shí)候,尤其是在作品的開頭部分,他們一定會(huì)播放一些和自己的心境或者作品的氛圍相對(duì)契合的音樂,借此來尋找創(chuàng)作的感覺或者說狀態(tài)。在創(chuàng)作《九月火車》的時(shí)候,我棲身在西安建國(guó)路附近的一棟破樓里,一年內(nèi)先后八次把老板炒了魷魚,身上揣著一兩百塊錢和早已殘破的理想。為了忘記現(xiàn)實(shí)的窘境,或是修補(bǔ)自己對(duì)未來的憧憬,我把自己關(guān)在不足30平的出租屋,一邊循環(huán)播放著許巍,一邊把電腦鍵盤敲打得噼里啪啦響。像各位所看到的那樣,整部小說彌漫著一股濃濃的理想主義氣息,我覺得這股氣息和許巍是分不開的,說得準(zhǔn)確一點(diǎn),和2013年春天我所聽到的許巍是分不開的。
管季:很榮幸能與兩位大咖一起來完成這次訪談,感謝朝軍,感謝《九月火車》。應(yīng)該說《九月火車》是一部比較典型的雙主線小說,主線之一呢,是圍繞周鹿鳴、水芬小姨、喬雅、大葫蘆老漢等人展開的鄉(xiāng)村圖景,主線之二是以周劍鳴、蘇野、關(guān)琳、佴志全、唯佳等為主的小城青年成長(zhǎng)史。在閱讀的過程中,無論是哪一條主線上的故事,都讓我感受到強(qiáng)烈的理想主義色彩,讓我對(duì)自己曾經(jīng)的生活產(chǎn)生了深深的懷疑,我不禁有一種想重新活過的沖動(dòng),尤其是想重讀一次大學(xué)。但是,在臨近小說結(jié)尾的幾個(gè)章節(jié)里,小說中最具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物——周劍鳴,他在經(jīng)歷了女友的母親——也就是高干凌九鳳女士擺下的家宴之后,突然就冷卻了下來,選擇了“逃避”(請(qǐng)?jiān)试S我使用逃避這個(gè)詞,也許對(duì)他來說,離去未必是逃避),對(duì)此,我有點(diǎn)難以接受。但是周劍鳴的結(jié)局又似乎只能這樣……就這一點(diǎn),我想聽一聽你內(nèi)心真實(shí)的想法。
周朝軍:博士到底是博士,火眼金睛,第一個(gè)問題就抓住了周劍鳴這個(gè)人物的核心。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我在小說中借凌九鳳之口對(duì)周劍鳴有過一個(gè)簡(jiǎn)短的概括,她說,“周劍鳴是飛在天上的人,可是飛在天上的人終究還是人,一旦落了地,就不會(huì)有好結(jié)果的。我不能把女兒交給這樣的人,他可以是一個(gè)不世出的天才,卻一定不會(huì)是一個(gè)合格的丈夫。他是一個(gè)完全精神化了的人……”。對(duì)于這樣一個(gè)人,任何帶有煙火氣的結(jié)尾都是無法承擔(dān)這個(gè)人物的結(jié)局的,所以如你所說,周劍鳴的結(jié)局只能這樣,只能是離開。
管季:我讀過你的不少中短篇小說,現(xiàn)在又讀了這部長(zhǎng)篇,對(duì)你整體的創(chuàng)作,我有三個(gè)問題想問。第一,與同齡作者相比,你的小說語言是出類拔萃的,你是如何訓(xùn)練自己的語言功底的?第二:緊跟第一個(gè)問題,我注意到,你的語言風(fēng)格不是一成不變的,好像隨著不同的作品一直在變換,但是似乎又都能看出某種相同的氣息存在,請(qǐng)解釋下這點(diǎn)。第三:除了語言之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你的知識(shí)面,在閱讀你作品的過程中,尤其是閱讀你部分短篇小說的過程中,我感覺到自己的知識(shí)儲(chǔ)備在被你無情地碾壓。我十分好奇,你是怎么在有限的時(shí)間里完成這樣一個(gè)龐大的知識(shí)儲(chǔ)備過程的?
周朝軍:管博士,你這不是提問,你這是對(duì)我赤裸裸地表?yè)P(yáng)啊,我無法拒絕一個(gè)女博士如此真誠(chéng)的贊美,我全盤接受了。
第一:關(guān)于語言,我沒有過刻意的訓(xùn)練,但是從我開始寫作到現(xiàn)在,寫作這些作品的過程,無一不是一種訓(xùn)練。最初的訓(xùn)練應(yīng)該是在中學(xué)的教室以及宿舍里完成的,記得那時(shí)候我的語文老師要求學(xué)生每周完成一篇周記,幾百字就可以,但是我往往兩三天就能用光一本日記本。什么都寫,但多半是半途而廢的小說,而且還是長(zhǎng)篇的架構(gòu)。我的老師曾經(jīng)在課堂上說,看我一個(gè)人的周記比看全班同學(xué)的周記工作量還要大。我中學(xué)幾年寫過的不成型的作品,遠(yuǎn)比我已經(jīng)發(fā)表的作品要多,從這一點(diǎn)上來看,我屬于笨鳥先飛的類型,以前的我還是挺用功的。
第二:語言風(fēng)格的問題,我是這樣看的,每一部作品都該有它自己獨(dú)特的氣息,語言應(yīng)該盡可能的去服務(wù)、去契合這種氣息,所以在不同的作品中變換語言風(fēng)格是必須的。另外,同一個(gè)作者,他在不同環(huán)境、不同心理狀態(tài)下的感覺也是不同的,比如我在家里的時(shí)候,我的心情就是比較放松的,寫作速度會(huì)很快,但是在廣州,我很難沉下心來,往往處于一種焦灼的狀態(tài)。不管是放松還是焦灼,這些都會(huì)滲透到你當(dāng)時(shí)所寫作的作品中。再者,比如我前面和浩哥談到的,比如音樂啊,或者你當(dāng)時(shí)正巧閱讀到的某部書籍的氣息啊,這些也都會(huì)影響到你正在創(chuàng)作的作品。也就是說,一部作品的風(fēng)格是帶有它的偶然性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常說,我們明明構(gòu)思的是這樣一個(gè)東西,但寫出來的卻成了那樣一個(gè)東西。但是,一個(gè)作者自身的氣質(zhì)是很難改變的,作者自身的氣質(zhì)是決定一部作品氣質(zhì)的關(guān)鍵。所以,一個(gè)作者的風(fēng)格無論如何改變,你總是能感受到同一股氣息的存在,這是肯定的。
第三:關(guān)于知識(shí)儲(chǔ)備這個(gè)問題,如果扯開了談,那應(yīng)該是一部專論。簡(jiǎn)單的說,我認(rèn)為一個(gè)人成年以前的閱讀是最可靠的,它構(gòu)成一個(gè)人知識(shí)結(jié)構(gòu)中最堅(jiān)實(shí)、最基礎(chǔ)的一部分,成年以前的閱讀,吸收得快,記憶穩(wěn)固,往往能銘記一輩子。我成年以前的閱讀確實(shí)比一般人要多,這么說吧,如果一本書以30萬字計(jì),我中學(xué)期間,每周能讀兩三本,周末的時(shí)候,一天能讀一本。你可能要問,你不用上課嗎?哈哈,我高中階段還真是基本不上課。坐在課堂上,別人上課,我看小說,回到宿舍,別人睡覺,我打手電繼續(xù)看小說。有時(shí)怕打擾別人,我躲在廁所里看,往往是快天亮了,我才回到宿舍睡覺。睡兩三個(gè)鐘頭,到課堂上繼續(xù)看。到了高三更瘋狂,上課時(shí)間我直接爬到操場(chǎng)上的樹上去看。這得感謝我的語文老師,是她對(duì)我的班主任說,“這個(gè)孩子你別管,他有他的目標(biāo)。”感謝我的語文老師,好人一生平安,哈哈哈。
管季;你在前言中所說,《九月火車》不是一部愛情小說,但小說中也還是寫到了幾對(duì)戀人,我發(fā)現(xiàn)一個(gè)有意思的現(xiàn)象,就是這幾對(duì)戀人,無一例外地是男小女大。另外,我看到此前有讀者給你開玩笑,問你是否有寡婦情節(jié)(好尷尬呀),比如小說中的水芬、陳麗云、芳姐、姚雪然全部是寡婦,這是巧合還是一種寫作中的“無意識(shí)”?
周朝軍: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你這是揭短呢,哈哈。我不避諱,因?yàn)閭€(gè)人的身世原因,我對(duì)母愛有一種極度的渴望,這導(dǎo)致我在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中,女主人公都或多或少的被賦予了一些母性的光輝,幾對(duì)戀人中,基本都是男小女大,這是一種無意識(shí)的表現(xiàn),可以為弗洛伊德心理學(xué)提供很好的范本。至于說寡婦情節(jié),我是沒有的,這不過是男小女大設(shè)置中的一種偶然,有過婚姻經(jīng)歷的女主比沒有過婚姻經(jīng)歷的男主年齡大,這很好理解。
管季:小說中周鹿鳴兄弟倆實(shí)際上是兄妹6人,小說中對(duì)其他4人并未提及,能解釋下是為什么嗎?另外,小說中“大舅”這個(gè)角色讓我深深地感動(dòng),但是在小說中“父親”的位置上為何安排的是大舅,請(qǐng)簡(jiǎn)單解釋一下。
周朝軍:這依舊是個(gè)人身世問題,我個(gè)人現(xiàn)實(shí)中就是兄弟姐妹6人,我6個(gè)月大就被過繼給了我的單身的大舅,我不知道父母之愛是什么,我小時(shí)候只有大舅、二舅、二姨、三姨這些人疼我。
管季:這部小說完稿于2013年的西安,在你另一部小說的前言里,你說起過你在西安的生活,那一年你先后8次被老板開除,和前女友一起過著十分窘迫的生活。我想問一下,窘迫的生活對(duì)你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周朝軍:三位老師真是默契,你們的好些問題都比較接近。前面談過,寫作時(shí)的環(huán)境和心境都會(huì)投射到作品中,2013年的我,只能用窘迫形容,我想不出別的詞。這種窘迫投射到作品中,可能就是周鹿鳴那種堅(jiān)韌的性格,可能就是“高干子弟愛上裝卸工”這種帶有意淫色彩的戀愛模式。這就好比有過勞改經(jīng)歷的張賢亮,他的小說中,男主總是在女主那里得到精神和肉體的救贖。有學(xué)者概括這叫“落難才子遇佳人”模式,古典小說中很常見,比如《李娃傳》《紅拂女》、《西廂記》,再比如《聊齋志異》中那些窮秀才與美麗的狐仙、鬼女的愛情。
管季:你對(duì)汶川地震的描寫,讓我想起了評(píng)論家楊慶祥對(duì)80后作出的一個(gè)評(píng)價(jià),他說80后是沒有歷史感的一代,直到汶川地震發(fā)生,這個(gè)事件凝聚起整個(gè)這一代人的歷史感和責(zé)任感。讀你的小說我就有這種感受,小說中那些不羈的年輕人,也都是80后,他們好像在震后突然就成熟了,就開始重新思考了。汶川地震那年,你應(yīng)該剛剛成年,談一下汶川地震對(duì)你和你的這部小說的影響吧。
周朝軍:我寫汶川地震是比較刻意的。你說得對(duì),我筆下的人物不能老是那么的激揚(yáng)青春,他們要成熟,要認(rèn)識(shí)人生,認(rèn)識(shí)社會(huì),我要讓讀者看見他們的擔(dān)當(dāng),于是我就把汶川地震寫了進(jìn)來。當(dāng)然這也是無法回避的一個(gè)事件,這部小說的時(shí)間跨度從2006年到2011年,08年汶川地震,那么大的事,任誰都回避不了,必須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