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王威廉:小說既是喚醒也是關乎人心的修煉
更新時間:2018-08-30 來源: 新青年周刊

多年以前,作家王威廉《非法入住》一刊出,即被《北大評刊》認為是“現代主義小說在中國瓜熟蒂落的開端”。此后,從《內臉》《第二人》,到《鯊在黑暗中》《聽鹽生長的聲音》,閱讀起來都讓人有了一種難得的更加開闊的生命感受。今天的網絡小說賣得非常好,有很多讀者,影響力非常大,陳培浩把這類寫作稱為“順時針寫作”,因為它順應了我們的時代,順應了很多人的閱讀要求,而王威廉是屬于“逆時針寫作”的。王威廉認為,現實文化確實是順時針的,順著我們的欲望推著我們往前走,不斷地給我們挖坑,然后又填滿,把我們推向無限,但反觀人文主義話語,它教給我們的核心就是克制,“克制就是要逼迫著你要逆時針地去成長,你的生命才會變得豐富起來。”
王威廉,曾就讀于中山大學物理系、人類學系、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現兼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創意寫作專業導師。曾在《收獲》《十月》《花城》《作家》《散文》《讀書》《詩刊》等發表小說、散文、評論等作品,被各類選刊、選本大量轉載。著有長篇小說《獲救者》,小說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生活課》《倒立生活》《北京一夜》等,并翻譯為英、韓、俄等文字。曾獲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首屆“文學港·儲吉旺文學大獎”、十月文學獎、花城文學獎、有為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藝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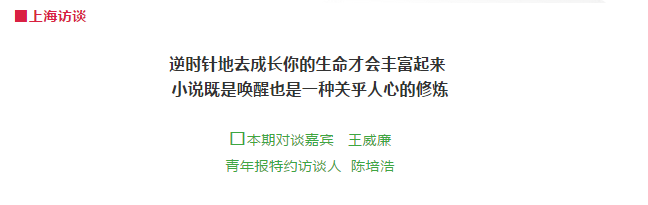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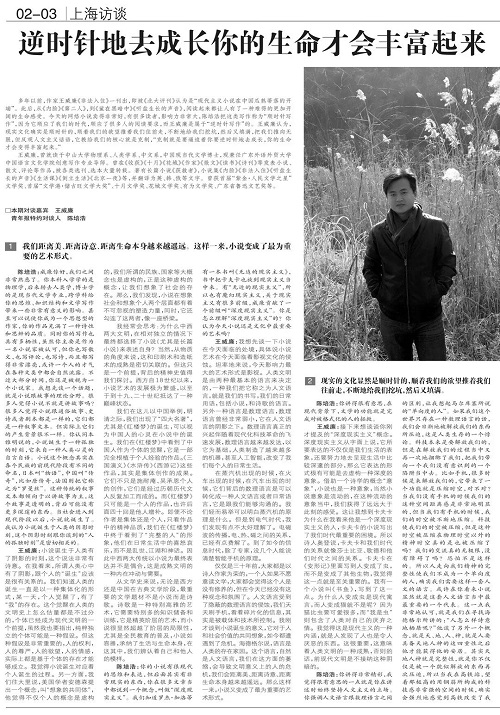

我們距離美、距離詩意、距離生命本身越來越遙遠。這樣一來,小說變成了最為重要的藝術形式
陳培浩:威廉你好,我們之間非常熟悉了。你本科入學學的是物理學,后來轉去人類學,博士學的是現當代文學專業,跨學科給你的思維、知識結構和文學寫作帶來一些非常有意義的影響。甚至可以說使你成為一個思想型的作家,你的作品充滿了一種詩性和思辨的品質。同時你的寫作也具有多棲性,雖然你主要是作為一名小說家被認可,但你也寫散文,也寫評論,也寫詩,而且都寫得非常漂亮,或許一個人的才氣在各種文類中都會自然流露。不過大部分時間,你還是被視為一個小說家。我想先談一個話題,就是小說跟故事的理論分野。很多人覺得小說不就是講故事嗎?很多人覺得小說跟通俗故事、史詩或者劇本都是一樣的,它們都是一種敘事文本。但實際上它們的產生背景很不一樣。你認同本雅明說的,小說誕生于一種孤獨的時刻,它來自一種人類心靈的自言自語。小說這個概念其實在各個民族的前現代階段有不同的命名,日本叫“物語”,中國叫“傳奇”,比如唐傳奇,法國則把它稱之為“羅曼絲”。這種傳統的敘事文本都傾向于以講故事為主,這個故事是透明的,背后可能沒有更多深邃的東西。當社會進入到現代階段以后,小說就誕生了。我認為小說誕生于人類的陰影時刻,這個陰影時刻跟你談到的“人的孤獨時刻”是密切相關的。
王威廉:小說誕生于人類有了陰影的時刻,這個說法非常有詩意。在我看來,所謂人類心中有了陰影,跟個人的“誕生”應該是很有關系的。我們知道人類的誕生一直是以一種集體化的形式,某一天,個人覺醒了,有了“我”的存在。這個覺醒在人類的文明史上怎么估量都是不過分的,個體已經成為現代文明的一個前提,雖然我也要指出,純粹獨立的個體可能是一種假設。但這種假設是非常重要的,人的權利,人的尊嚴,人的欲望,人的情感,實際上都是基于個體的存在才能夠成立。我覺得小說誕生對應著個人誕生的過程。另一方面,我們往大里說,美國學者安德森提出一個概念,叫“想象的共同體”,他覺得不僅個人的概念是虛構的,我們所謂的民族、國家等大概念也是虛構的,正是這種虛構的概念,讓我們想象了社會的存在。那么,我們發現,小說在想象社會和想象個人兩個層面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塑造力量,同時,它還勾連了這兩者,像一座橋梁。
我經常會思考:為什么中西兩大文明,在相對獨立的情況下最終都選擇了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來表述自身?當然,從物質的角度來說,這和印刷術和造紙術的成熟是密切關聯的。但這只是一個前提,背后的精神史值得我們探討。西方自18世紀以來,小說藝術的發展極為繁盛,以至于到十九、二十世紀抵達了一種巔峰狀態。
我們在這兒以中國舉例,明清之際,我們出現了“四大名著”,尤其是《紅樓夢》的誕生,可以視為中國人的心靈在小說中的誕生。我們在《紅樓夢》中看到了中國人作為個體的覺醒,它是一部完全根植于個人經驗的作品。《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這些作品,其實是集體創作的成果。它們不只是施耐庵、吳承恩個人的創作,它們是經過歷朝歷代文人反復加工而成的。而《紅樓夢》只可能是一個人的作品,也許后面四十回是他人增補。即便不論作者是集體還是個人,只看作品中的精神品質,我們在《紅樓夢》中終于看到了“完整的人”的形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而不是亂世、江湖和神話。因此中西兩大傳統以小說為最終表達并不是偶合,這是成熟文明的一種內在沖動與需要。
從文學史來說,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在古典文學階段,最重要的文學題材不是小說而是詩歌。詩歌是一種特別高雅的藝術,它需要特別多的知識儲備和訓練,它是精英階層的藝術,而小說很顯然超越了階層的局限性,尤其是全民教育的普及,小說如容器,承納了生活與生命本身,在這其中,我們辨認著自己和他人的模樣。
陳培浩:你的小說有很現代的思維和表達,但后面其實有非常現實的東西,你在很多文章當中都說到一個概念,叫做“深度現實主義”。我們知道羅杰·加洛蒂有一本書叫《無邊的現實主義》,書中把卡夫卡也放到現實主義當中來。有“無邊的現實主義”,所以也有魔幻現實主義,關于現實主義有很多前綴,威廉貢獻了一個前綴叫“深度現實主義”。你是怎么理解“深度現實主義”的?你認為今天小說還是文化中最重要的藝術嗎?
王威廉:我想先談一下小說在今天面臨的處境,具體說小說藝術在今天面臨著影視文化的侵蝕。坦率地來說,今天影響力最大的藝術形式是影視。人類文明是由兩種最基本的語言來決定的,一種我們把它稱之為人文語言,就是我們的書寫,我們的日常用語,包括小說,和詩歌的語言。另外一種語言是數理語言,數理語言曾經非常弱小,它在人文語言的陰影之下。數理語言真正的興起伴隨著現代化科技革命的飛速發展,數理語言越來越發達,以它為基礎,人類制造了越來越多的機器,甚至人工智能,改變了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在蒸汽機出現的時候,在火車出現的時候,在汽車出現的時候,它們背后的數理語言是可以轉化成一種人文語言或者日常語言,它是跟我們能夠溝通的。我們輕而易舉可以明白蒸汽機的原理是什么。但是到電氣時代,我們發現有點不太好理解了。電磁波的傳播,電、熱、磁之間的關系,已經有點費解了。到了如今的信息時代,除了專家,沒幾個人能說清楚智能手機的原理。
僅僅是三十年前,大家都是以詩人作家為榮的,一個人如果不愿意讀文學,大家都會覺得這個人是沒有修養的,但在今天已經沒有這種觀念和氛圍了。人文語言受到了隱蔽的數理語言的侵蝕,我們天天刷手機,看著碎片化的信息,其實是被載體和技術所控制。我剛才談到小說誕生的意義,它對于人和社會價值的共同想象,如今都遭遇到了危機。海德格爾說,語言是人類的存在家園。這個語言,自然是人文語言,我們在這方面的萎縮,會導致文明意義上的人的危機,我們會距離美、距離詩意、距離生命本身越來越遙遠。那么這樣一來,小說又變成了最為重要的藝術形式。

現實的文化顯然是順時針的,順著我們的欲望推著我們往前走,不斷地給我們挖坑,然后又填滿。
陳培浩:你講得很有意思,在現代背景下,文學的功能就是完成對被格式化的人的拯救。
王威廉:接下來想談談你剛才提及的“深度現實主義”概念。深度現實主義從字面上說,它所要表達的不僅僅是我們生活的表象,還要努力地去呈現生活中比較深邃的部分,那么它表達的形式極有可能是去虛構一種深度的意象。借助一個詩學的概念“意象”,小說也是一種意象,當然小說意象是流動的,在這種流動的意象當中,我們獲得了遠遠大于此刻的感受。這讓我想到卡夫卡為什么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深度現實主義的人,卡夫卡的小說寫出了我們時代最重要的困境。所以詩人奧登說,卡夫卡和我們時代的關系就像莎士比亞、歌德和他們時代之間的關系。卡夫卡在《變形記》里面寫到人變成了蟲,而不是變成了其他生物,我覺得這一點就是至關重要的。我有一個小說叫《書魚》,寫到了這一點。為什么人變成蟲是現代寓言,而人變成貓就不是呢?因為貓比蟲要可愛很多,而“我是蟲”則包含了人類對自己的厭棄之情。我覺得這是現代主義的一種內涵,就是人發現了人也是令人厭惡的東西。這很重要,這意味著人類文明的一種成熟,否則的話,前現代文明是不接納這種陰暗的。
陳培浩:你講得非常精彩,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你在講述時始終堅持人文主義的立場。你強調人文語言跟數理語言之間的區別,讓我想起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如果我們這個世界只存在一種數理語言的話,我們會日漸地被解放我們的東西所壓迫,這是人類生存的一個悖論。科技本來是要解放我們的,但是在解放我們的過程當中又再一次地捆綁了我們,把我們帶向一個我們沒有意識到的一個陷阱當中去。比如手機,很多時候是來解放我們的,它帶來了一個功能就是壓縮時空,對不對?當我們沒有手機的時候我們的這種空間距離感是非常地明顯的,但當我們有手機的時候,我們的時空被不斷地壓縮。科技使我們的時空被壓縮,但是這種時空被壓縮在物理時空以外的精神時空真的是也被壓縮了嗎?我們的交流真的無極限,沒有障礙了嗎?恐怕不是這樣的。所以人走向我們精神的完整性使我們不成為一個單向度的人,確實我們需要這樣一套人文的語言。或許在你看來小說顯然就是這套人文語言當中最最重要的一個代表。這一點我非常地認可,就是我們在尋找海德格爾所講的:“人怎么樣詩意地棲居呢?”他談了另外一個概念,就是天、地、人、神,就是人要具備天地人神的這四重性之后他才能獲得他的安居。其實天地人神就是完整性,就是你不僅僅是被一個貌似解放的東西再次壓迫,所以當我在高鐵站,望著那極高的用鋼筋所構成的科技感非常強的空間的時候,確實會強烈地感覺到高鐵改變了我們的空間,這是實際存在的。那誰創造了高鐵呢?一定是操持著數理語言這班人所創造出來的。所以某種意義上它確實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是如果真的沒有人文語言,只有這套數理語言,這種世界真的會更好嗎?恐怕不是。所以我們看到那樣一個科技感很強的空間當中它也會努力地要融入人的一些東西,要和你的情感發生共鳴,而不是讓你覺得冰冷無助。那么在這個意義上,小說確實誕生在人類文明的最高階,在這一點上我現在的論調有點挽歌式的悲觀。因為人類科技已經非常發達了,我們作為人處在一種受壓迫的狀態。
王威廉:人類要詩意地棲息在大地上,但是我們失落了這種人文語言的詩意,我們就會變成現代的原始人。如一個著名的網絡段子所說的,當看到大海的時候只會說:“大海真大啊!”人類豐富的情感世界被簡化了。所以以前的哲學家都說人的內心等同于一個宇宙。葡萄牙詩人佩索阿更是說:我的心略大于宇宙。
陳培浩:我談過兩個概念,叫做“逆時針寫作”和“順時針寫作”。什么叫做“順時針寫作”,就是我們知道時針滴答滴答地順著時鐘走,有的逆著時鐘走,那么什么叫“順時針寫作”?今天的網絡小說賣得非常好,有很多讀者,影響力非常大,我把這類寫作稱為“順時針寫作”,因為它順應了我們的時代,順應了這個時代很多人的閱讀要求。但在我看來人類的尊嚴常常就出現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時刻,這就是你的“逆時針寫作”。你在我們這個時代依然在強調人文主義,依然在強調寫作的內在深度,依然在強調人類的尊嚴,很多時候被俗人認為是可笑的。我非常喜歡詩人辛波斯卡的一首詩:我偏愛無拘無束的零勝過阿拉伯數字后面的零。這句話是很有意思的,你想想我們日常的思維,給你10萬,你說很好,那我在你的10后面再加一個0,給你100萬,你會覺得太好了。這是日常的思維,是現實的功利的思維。但是辛波絲卡反其道而行之,她說:我偏愛無拘無束的零,這個0不在任何1的后面,所以它沒有產生大還是小的選擇,因此它是自由的。這樣的自由對生命是至關重要的。
回到深度現實主義,我認為作為小說家很難得的事情是他不僅會寫小說,而且他有自己的小說觀。小說家自然都會寫小說,但很多人的寫作才華是老天給他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為什么要寫小說,也不知道他自己為什么會寫小說。他下筆千言,能講很好的故事,但是他卻不知道小說是什么。所以做一個自覺的小說家很重要的一個標志是他知道小說是什么,他能夠給小說一種命名,他知道自己的小說要往哪邊去。我覺得你就是一個有自己小說觀、知道自己的寫作往哪里去的作家。
王威廉:你剛才說的辛波斯卡的那句詩我也很喜歡。這就是我剛剛說的人文世界跟數理世界之間的這種分野,我們可以把這個自由無束的零視為人文語言中的一個零,這個零是什么呢?對我們來說其實就是空白、是虛無,也是無限的可能性,但如果是在數理語言的領域,那就是什么都沒有,或是表達計量的多少。這首詩還有另外兩句特別有名,大意是“這個世界本身就是荒謬的,但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多于不寫詩的荒謬”。我覺得這句詩簡直石破天驚,是對你“逆時針寫作”說法的最佳回應。
我把話題繼續拓寬一下。實際上我覺得數理語言以及它所代表的科技,它更多的是跟消費主義結合在一起,不斷地制造欲望,然后再讓龐大的機器不斷生產重新滿足我們的欲望。很多欲望是我們本來沒有的,但被制造出來,然后再去滿足我們,讓我們欲罷不能。就像蘋果手機,本來你有iPhone6就很高興了,它非要出plus;等你買到iPhone8,似乎頂天了,但現在iPhoneX就出來了。它們的差別大嗎?客觀想想,其實不大的。但你有了想要的欲望。我們都看過新聞,知道竟然有人愿意賣腎去買蘋果手機!這就是消費主義跟科技主義結合在一起對我們奴役的現實。這種現實的文化顯然是順時針的,順著我們的欲望推著我們往前走,不斷地給我們挖坑,然后又填滿,把我們推向無限,也榨干了價值。但反觀人文主義話語,它教給我們的核心就是克制。克制就是要逼迫著你要逆時針地去成長,你的生命才會變得豐富起來。如果你是順著它走的話,你的生命永遠不能成熟。那么,用小說家狄更斯的話來說今天依然很適合,這依然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依然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那取決于你自己,就是個體生命的成熟。尤其在今天這個道德渙散時代,沒有太多外力去干擾你的人生選擇,那你對自己的生命就需要肩負起更加重大的責任。

沒有了審美和詩意的傳統,人活得失去了對美的感受能力,這對生命來說是莫大的諷刺,是對生命的一種否定。
陳培浩:我們的個體自由空間的確有所拓寬,因此虛無也在隨之增長,那你覺得在今天作家的藝術責任應該是怎樣的呢?
王威廉:我覺得今天的作家一定要發出自己特別獨特的聲音,這是最重要的。你如果特別喜歡一個作家你會發現他的敘述腔調跟其他作家是不一樣的,你會一眼就認出他來。比如說余華,他的《活著》,他的《許三觀賣血記》,那種敘述方式一看就知道是余華的。為什么余華后來的《兄弟》《第七天》備受質疑,不僅是因為他大量引用了新聞素材——我倒覺得那個在其次,反而是他的一個創新——我覺得最顯著的是他作為一個作家的獨特聲音在消散,這是很可怕的。最讓我難忘的是余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里面充滿了一種詩意的幽默的個人聲音。在那樣的聲音里面,它講的故事是什么可能不太重要了,它用一種迷人的私語把你帶到了另外一個空靈的世界里面。蘇童的小說《我的帝王生涯》也是如此。莫言的語言可能在許多人看來沒有那么優雅,但同樣,其中有著他獨特的聲音。他那種滔滔不絕的氣勢,奇妙的通感和比喻,龐大的排比句泥沙俱下,構造了莫言獨特的語言世界。說到底,小說家的聲音背后實際上站的是真正的個人,他發出了獨特的聲音,這個獨特的聲音意味著個體的生命是不能被集體、消費和科技所淹沒的。個體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證明自己的存在,我覺得這欲望是生命最本質的欲望,是不可磨滅的、最本質的生命欲望。
你讀那些偉大的小說,比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魯迅的,你的腦海里會被一種聲音所喚醒,他的聲音喚醒了你的聲音。你有了自己內心的聲音,你也獲得了自己生命的一種抵達。小說是一種喚醒,它的喚醒功能跟其他的社會科學知識都不一樣。小說是一種特殊的知識,一種關乎心靈和生命的知識。但是它在科技思維的劃分下,喪失了自己的位置。在大學的學科里面,人文學科被壓縮到越來越小的位置。而我們古代的書院,完全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它通過人跟人之間的耳濡目染、口傳心授,把人文的火焰延續下去。而如今已經萎縮的大學中文系竟然還會告訴學生,你不是來寫作的,是做研究的。這是荒謬的事情,寫作和研究是對立的嗎?一個不懂寫作的人,如何研究寫作?文學的論文也采用科技論文的模式,要有結論和嚴密邏輯,這都是我們時代的荒誕景觀。
陳培浩:我身處高校,的確對此感同身受,我也一直在尋求打破邊界,比如我一直寫詩,就是為了保全我的感性審美,否則,我會感到非常壓抑。
王威廉:今天這個時代抑郁癥是很多的,人們內心的隱疾得不到抒發,人沒有一個完備的世界觀,他對這個世界整體失去了判斷,他對這個世界產生了失望。人為什么會失望?就是因為他與世界之間逐漸失去了聯系,這時候他就會產生極度的絕望。小說既展示了這種絕望,同時也試圖去彌合人與世界的鴻溝,修復這種絕望。所以我覺得現代小說也關乎人心的一種修煉。也許現代小說沒有電視劇那么好看,沒有那么多精彩的情節,但是當你深刻體驗到現代小說的精神層面之后,你所獲得的內心觸動和精神收獲要遠遠大于那些情節很熱鬧的商業產品。現代小說給我們強大的精神空間,同時讓我們對各種類型的、現代的、后現代的藝術作品都產生極大的敏感度。我覺得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在審美上的成熟。這很重要,對于人來說,除了生存以外,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美學的維度。美學的維度可能甚至要大于宗教的維度。比如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宗教感不是特別強,但是為什么中國文明能夠生生不息,為什么我們現在仍然如此眷念著我們的五千年文明,就是因為我們的文明是一種高度審美化的文明。我們的古典教育稱之為詩教,這點在今天也需要延續下去。沒有了審美和詩意的傳統,一個人活得失去了對美的感受能力,這對生命來說是莫大的諷刺,是對生命的一種否定。
陳培浩:我對你剛才說的,想概括出兩句話:第一句是“語言即照亮”,第二句話是“小說即喚醒”。這恐怕是你的小說觀當中非常重要的觀念。現代主義不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奇奇怪怪的變化,語言作為對世界的一種照亮,我們發現了我們時代的虛無,同時我們也在超越這種虛無。你不斷地在強調小說跟個人的內心、個人的主體的關聯性,并由此出發,你認為小說必須要有一種個人的語調。我對這些都是很認同的,由此我想再說幾句我們今天該如何看待現代主義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
的確,卡夫卡已經寫出了《城堡》《變形記》這樣的小說,今天如果還只是停留在做卡夫卡回聲的層面上,是不夠的。我們要領悟現代主義的遺產,還是需要從人的精神困境中來思考它。你的寫作,歷來被認為是現代主義和中國經驗的一種獨特結合。好多年前,你的處女作《非法入住》一出來,就被《北大評刊》認為是“現代主義小說在中國瓜熟蒂落的開端”。這個判斷是相當準確的。你之后的小說,從《內臉》《第二人》,到如今的《鯊在黑暗中》,都體現了鮮明的現代風格。我在這里要提你一篇具有現實色彩的小說——《聽鹽生長的聲音》。這篇小說的背景是一個鹽堿地,鹽堿地就是不毛之地。鹽堿地有沒有生命呢?幾乎沒有。但是你這個小說中有一個很詩意的意象,主人公能夠聽到鹽堿地里邊的鹽在生長。鹽也具有生命,它在呼吸,在生長,也在傾聽,我讀到了一種更加開闊的生命感受和生命觀念。所以在你的寫作中,我確實看到了一個當代中國作家在接受現代主義資源的同時,也在尋找著一種中國式的或者說當代的現代主義的可能性,包括精神上的可能性還有寫作上的可能性。這樣的寫作自覺性,我希望在你的作品中能讀到更多。
(陳培浩,青年批評家,文學博士、副教授。)
■人物釋義
孤獨喚醒他的聲音
□張逸麟
不久前,作家王威廉作為主講者參加了一檔在線談話類節目,主題是“巨型都市與藝術想象”。當時王威廉一個人待在房間里,對著一個手機發表著自己的論述。
這個場景讓王威廉自己感到既有點荒誕,又有些親切。“我知道我的聲音一直在上傳到網絡上,有許許多多我看不見的朋友在聽,但是,我此刻的狀態,完全是自言自語的感覺,依然是封閉的。”王威廉在直播中說,“這讓我不禁想起德國哲學家本雅明說到的小說跟故事的區別:小說是誕生在孤獨之際的自言自語。”
可在王威廉看來,這種孤獨并不是封閉,不是自我設限,有時候更像是一種狂想。在狂想中尋找詩性,在狂想中進行思辨。
本科入學時,王威廉學的是物理學,對此他并不諱言自己當初的理想是成為愛因斯坦那樣的大科學家,他把愛因斯坦的畫像掛在床頭,希望與偶像一樣去發現世界的奧秘,去改變世界。可后來王威廉轉去人類學,最終在文學“定居”。這種跨界的經歷對王威廉的創作有著很深的影響,甚至可以說使他成為一個思想型的作家,作品充滿了一種詩性和思辨的品質。
詩性是王威廉一直追求的,無論是他的詩、小說還是散文。但是給讀者留下更深印象的是他作品中的思辨性,有人評價王威廉的作品的關照對象非常寬泛,而對于關照對象的生存現狀與精神狀態的深度表現,又體現了他對整個社會與人的關系的深入思考。
在科技飛快發展的當下,人類制造了越來越多的機器,甚至人工智能,改變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數理語言變得越來越強勢,而與生活、藝術息息相關的人文語言日漸式微,隨之也給人們帶來了危機和精神困境。“我們會距離美、距離詩意、距離生命本身越來越遙遠。”王威廉表示,“那么這樣一來,小說又變成了最為重要的藝術形式。”
小說往往就誕生于困境,誕生于危機,甚至誕生于絕望。比如卡夫卡在名作《變形記》里面寫到人變成了蟲,讓人感觸很深,而王威廉在小說《書魚》中也寫到了這一點,為什么人變成蟲是現代寓言,而人變成貓就不是呢?因為貓比蟲要可愛很多,而“我是蟲”則包含了人類對自己的厭棄之情,卡夫卡的筆鋒直插入現代社會的困境之中,才能產生如此強烈的共鳴。王威廉的許多作品也展現了對人類現世狀態與精神世界的凝思。
王威廉沒有在物理學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沒有在數理邏輯上去改變現實世界,卻努力在人文語言范疇,在文學世界中去探索,去喚醒。哪怕小說是孤獨之人的自言自語,但它也在尋找著另外一些孤獨的人,要喚醒他們的共鳴。許多偉大的作家都在用自己的聲音在喚醒著讀者,比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魯迅,這個獨特的聲音意味著個體的生命是不能被集體、消費和科技所淹沒的。王威廉也在努力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去完成屬于他的喚醒。
正如他在《倒立生活》中寫的那樣:我們生活中那些不可言說的東西、那些難以被理解和消化的東西都需要文學的溶液,沒有這種溶液,我們會活得越來越僵硬,我們的生命會像得了頸椎病似的痛苦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