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從異鄉到故鄉——陳再見小說研討會精要
更新時間:2020-03-24 來源:華夏雜志
陳培浩:陳再見是近年在廣東以至全國備受關注的青年作家,他的寫作,從最初的打工書寫,后來的縣城書寫,最近又有了新的變化。陳再見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講故事的人”,但他顯然有非常自覺的純文學堅守。或許他有能力通過網絡寫作獲得更多的現實回報,但他顯然另有自己的夢想和抱負。討論陳再見,繞不過他的“縣城”書寫。有人說,是賈樟柯的電影發現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縣城;陳再見家鄉有個樂隊叫“五條人”,他們出過一張頗有影響的專輯,就叫《縣城記》。這種專輯上有句宣言叫“立足世界,面向縣城”。這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般世界想象的秩序,是沿著村―鄉―縣―市―省―國―世界的等級軌跡遞進的,這個鏈條所隱含的等級秩序使人們習慣了“立足縣城,面向世界”的論述。其實,“立足縣城,面向世界”是現實邏輯,“立足世界,面向縣城”則是藝術邏輯,具體到陳再見小說,將世界性視野引入其縣城書寫中,可能會產生更大的格局。我們會發現,陳再見書寫的“縣城”與賈樟柯的“縣城”并不一樣,差異很大來自賈樟柯電影中九十年代的山西縣城雖然也有大量外界信息的進入,如港臺流行文化之類,但那個縣城基本是靜態而自足的,它有自身不變的邏輯。但陳再見筆下的縣城,表面看似乎只是無數中國縣城之一,但它已經置身于巨變流動的全球化秩序之中。這種流動的縣城并不僅僅是其自身,還沒有甩干凈鄉村的泥土,又倒映著種種全球化時代的本土化幻影。今天中國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所有的東西穩定的邊界都被打破了,你無法找到一個僅屬于鄉村的鄉村,也無法找到一個僅屬于城市的城市。今天農村里到處是玩快手、抖音的網紅青年,而即使是最繁華的城市,在CBD商業區以外不出五公里,必有另一片景象的城鄉接合部。所謂城鄉接合部,不就是藏身于城市中的縣城嗎?所以,對于今天的作家來說,不僅是書寫某個特定的縣城,而是書寫疊加在縣城上的鄉村和城市,書寫中國的縣城,便是在書寫縣城里的中國。

▲《青面魚》 陳再見/著
王威廉:對于故鄉的“愛意”,恐怕是最為流行的一種文學思潮。每個人似乎只要稍微有點文學愛好,都會忍不住贊美自己的故鄉。這是人類的一種本性,對于家園的眷念,是我們永恒的鄉愁。為了寄托鄉愁,我們自然要美化故鄉。但是,我很高興再見能這樣說:對自己的家鄉懷有恨意。尤其當我們長時間置身在家鄉的時候,誰沒有體驗到那種窒息的想要逃離的沖動?等到你真的逃離了之后,你又開始想念那里的一切。這種悖論怎么能不讓人心生恨意呢?只有文學能夠承載這種悖論的恨意。恨意綿綿,也是愛意綿綿。這就是人世間吧。我是希望在再見的小說中,能讀出那種恨意的細節,以及恨意的深度與寬闊。那么,說起來,打工,既是陳再見謀生的一種行為,也是他逃離家鄉的一種方式,他通過在異地的艱苦工作,與故鄉拉開了距離,但是寫作上卻更見親近了故鄉,實現了一種精神還鄉。我去過再見的故鄉,還在他故鄉的鄰縣扶貧過一年。我熟悉他筆下的風物,因而,我每每讀再見的小說,都似乎能聞見那淡淡的海風的腥味。他虛構的地理空間“扇背鎮”,里邊那些被他細膩描寫的吃食,有著鮮明的潮汕文化特點。很多論者都認為,小說家如果有一個地理意義上的“根據地”,那么他的寫作一定可以豐厚和持久。比如福克納,比如馬爾克斯……但是,我們這個時代,能讓我們徹底寄托情思的根據地越來越少了,因為劇烈的城市化進程讓傳統的社會結構在解體、在新生,鄉村不再是田園牧歌。這也是為什么這些年來鄉土小說迅速衰敗的原因。賈平凹的“商州”、閻連科的“耙耬山脈”、蘇童的“楓楊樹”,短暫地構成過中國當代文學的地理學,但是如今,這些作家的寫作一直在調整,那些“文學地址”也沉潛進了文學史的記憶中。在這樣的背景下看再見的小說,我覺得更加清晰。再見的故鄉與其他地方不大一樣,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不像別的省份,人口被抽空,而廣東這里,是人口在大量注入,比如我去再見的家鄉陸豐(縣級市),我好幾次打車,出租車司機都是外省人,這在別的地方的小縣城,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再見寫下的故事有著相當強的當代性,其中飽含著這個時代的復雜癥候。像吸毒、犯罪、人口買賣等等,再見的小說都有所涉及。因而,再見是幸運的,他的根據地依然“有效”,我特別期待他的寫作能繼續深入他的故鄉,用現在的熱話說:為我們帶來更加豐富的“中國故事”。
鄭煥釗:我在閱讀再見的小說中,腦子里出現了賈樟柯的電影。縣城經驗是中國經驗最寶貴的精神資源,也是當下中國人精神狀態的最重要的載體。作為最具代表性的縣城經驗的寫作者,賈樟柯的電影以一個較大的歷史維度,通過青年身份的變遷,來呈現中國社會文化的轉型過程。他頗具策略性地地將人物的節點與中國當代歷史的重要時刻緊密結合起來,從中國闡釋中國的變化,而在《天注定》等電影中,賈樟柯也呈現了社會底層的脆弱尊嚴及其如何在一個時代中被輕易碾壓,如何轉化成社會的暴戾。作為一個參照,近來陳再見的小說聚焦縣城眾生在這個時代的靈魂空虛、精神潰敗與救贖的絕望。如《皮小姐》中梅朵拉姆充滿宗教神秘色彩的“巫婆”形象,一個無所不能的角色卻最終呈現為對自身的“束手無策”,顯示了宗教救贖的不可能性。《去滿洲里》書寫了一個試圖在他鄉進行靈魂救贖,但這一過程,是一種離開了安全地方的無所適從的生命感受。而在《陵園舞者》中,靈魂空虛籠罩在每個人身上,而在欲望的呢喃與生命的掙扎與沉淪中,每個人都無法幸免,而T恤上面的切·格瓦拉符號,作為一個革命者的符號,在小說中不管對女兒李一明,還是韓驍來說,只不過是一個劣質的青春叛逆形象被消費,意味著底層革命的道路已經被青年本身所消解。在這種空虛與絕望中,陳再見也寫出了底層脆弱的尊嚴,比如《馬尾街死人事件》在一個連環的殺人事件的背后,則是兇手何一洲對女友黃素如自始葆有的那樣一種非常溫馨的日常的幻覺,正是這種幻覺在現實中所遭受的背叛,摧毀了他最后的一絲尊嚴,這溫暖的幻覺與脆弱尊嚴,及其與暴力的行為所構成的復雜關系,讓陳再見的小說對縣城轉型中的精神書寫具有了復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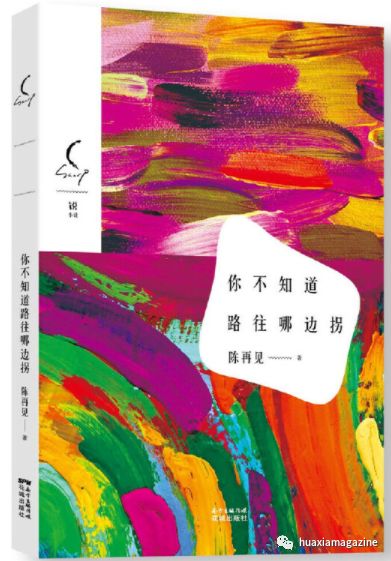
▲《你不知道路往哪邊拐》 陳再見/著
楊丹丹:從一般意義上而言,陳再見被歸入底層文學作家的行列,貼上底層作家的標簽,但從我的閱讀經驗和閱讀體驗來看,陳再見與常規意義上的底層寫作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尤其是在表述方式上呈現出獨特性。絕大多數的底層寫作在表述底層的時候往往采用三種方法:一、對底層苦難生活進行擴大化和夸大化處理,在無限的苦難疊加中,激起讀者對底層的同情和悲憫;二、將底層作為宣泄負面情緒的載體、中介和通道,底層寫作講述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底層能夠承載多少非理性的情緒;三、將底層寫作與左翼文學勾連起來,發現其中醞釀的革命因素和反抗精神。這三種表述方式將底層寫作簡單化、固定化和模式化,為底層寫作設置了牢籠和陷阱。但陳再見的文學寫作卻使底層寫作變得更為豐富性和多樣性,陳再見拒絕將底層和底層的苦難生活作為滿足獵奇心態、非理性情緒宣泄和對抗社會的文化資本,而是努力在客觀呈現底層現實生活的同時,發現底層社會牽扯出來的人、人性、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社會關系的豐富性。例如,陳再見的短篇小說《陵園舞者》講述關于背叛婚姻的故事,但我們無法將背叛婚姻的行為放置在傳統倫理框架中去評判,男女主人公的背叛因為與身體的欲望并不存在直接聯系,而是與個體的生活體驗和精神依賴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系。同時,小說設置了一個富有意味的情節:女主人公在與情人偷情的時刻,她的初中生女兒正在與一群少年發生肉體關系。在同一時刻發生在母女身上的偷情和淫亂事件,讓女主人開始正視和反思自我行為的正當性,但女兒卻以無所謂的態度對母親的傳統倫理反思進行了嘲弄和解構。在反思和解構之間,“性”成為代際沖突的場域,從而使人性變得多樣而復雜。陳再見的小說在敘述形式上擯棄敘事形式的華麗和炫技,敘事形式平實、自然而溫婉,但正是這種敘事形式支撐起陳再見小說故事的獨特性。陳再見小說在敘述語言、敘述時間和敘述節奏上與同代作家相比較都存在獨特的差異性。

▲廣東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
馮娜:陳再見早期的小說我讀之甚少,所以我一進入他的文本就跳過了批評家說的“打工文學”那個文學階段,直接進入了他關于城市書寫的近期小說;另一方面,這說明他是一個具有成長性的小說家。他的近作給我一個共同感受是,這是一個故事講述能力很強的小說家,也是一個擁有極其蕪雜、混沌的生存、生活經驗的小說家。之前王威廉對他生活經歷的描述,證實了我這種感受。陳再見的小說有一種不多見的親和力,好像他筆下故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故事中的人物是我們的鄰人或者每天與我們擦肩而過的路人。就像《陵園舞者》這篇小說,他講述的好像就是中國當下隨便一個城市都會發生的故事,故事里有背叛、有罪行、也有非常的殞命,但就是這樣一個混雜著黑暗元素的故事,仿佛就發生在隔壁房間。這篇小說也讓我聯想起愛爾蘭小說家克萊爾.吉根的《南極》,它雖然不似《南極》那般冷酷,但擁有相同的細密、冷靜的觀察力和對故事整體的把控能力。人的命運感和死亡問題一直是陳再見的書寫中關注的“母題”。《陵園舞者》《馬尾街死人事件》等小說中都寫到常人的非常死亡。一個嚴肅的作家必然要思考生與死的命題,在陳再見關于死亡的敘事里我經常會感到一種“猶疑”,我認為這種猶疑來自他的生活經驗,更來自他不愿意墜入虛無的一種書寫努力。里爾克曾說,詩并不像一般人所說的是情感(情感人們早就很夠了),詩是經驗。我想小說亦是如此,從一個具有魔幻氣質的鄉村穿越城鄉接合部、再到高速發展的現代大都市的經驗是一個小說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饋贈,我希望陳再見珍惜這種經驗,寫出更具獨特品質的小說。
唐詩人:2013年我來到廣州后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陳再見小說評論,那時候陳再見也是剛剛冒起。此后他一發不可收拾,寫了非常多作品,剛才威廉說陳再見的量大,的確是這樣,這些年再見估計寫了不下一百萬字了吧,有一段時間好像是一個月內就好幾篇刊出。這種速度,也讓我的閱讀落后了,導致我沒能完整地追蹤他的寫作。但我從最開始時候的觀感,聯系到最近他小說集《青面魚》中的作品,以及他最新的“縣城”系列作品,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一個作家的成熟。他的寫作已變得特別豐富,這種豐富,包括題材、風格和技術。題材上,他不再局限于寫自己的故事,還能寫出很多他人的故事。小說集《一只鳥仔獨支腳》里面主要還是寫陳再見的故鄉人事,《喜歡抹臉的人》集中的是深圳底層世界的一些人物遭遇,這些或許都更接近一個打工作家的“標簽”。而最近的《青面魚》等,其實已經突破了這些標簽,“縣城”系列小說,也更清晰地表達出陳再見書寫中國故事的宏大抱負。風格、技術上,開始時陳再見慣用的還是比較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是老老實實講故事,而最近的《馬戲團即將到來》《陵園舞者》等,發揮他擅于講故事的能力的同時,也加入了很多獨屬于短篇小說的藝術特征,比如精巧的結構、思想色彩強烈的敘述等。從這種豐富性層面來看,我覺得陳再見其實是一個特別值得期待的作家。只要把這些能力融合起來,把所有題材上的、技術上的東西打通,再見可以從目前的作為一個會講故事的優秀青年小說家,很快躍升為一個會講故事的路遙式、莫言式的大作家。我私下里其實一直期待著再見寫出一個大長篇來,那很可能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平凡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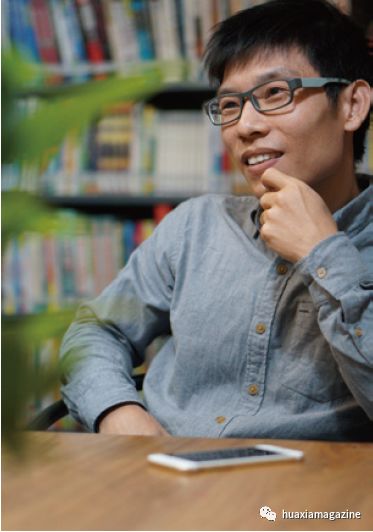
▲陳再見:1982年生于廣東陸豐;已在《人民文學》《當代》《十月》《中國作家》等刊發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新華文摘》等選刊選載;出版有長篇小說《六歌》,小說集《一只鳥仔獨支腳》《喜歡抹臉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邊拐》《青面魚》《保護色》;榮獲《小說選刊》2015年度新人獎。
陳再見:謝謝各位同道。我很喜歡本次研討會,都做足了準備,無論是褒獎還是批評,都直接有效。寫作多年,有所長有所短,我自覺是門清的,有時看到一部好小說,閱讀起來就相當恐懼,那等于就是在消磨自己繼續寫下去的動力。這時候,我也許需要多看幾篇平庸之作,才能重獲信心。想想都覺得可笑吧。不過這些年,我寫作的方向大抵沒什么改變,這可能得益于當年閱讀的起點就比較高。王小波、余華等先鋒作家是我寫作的引路人,跟隨他們的腳步,方向上不曾有過懷疑,倒是在寫作題材、角度、手法上有諸多改變和體悟,比如從打工題材到鄉土題材再到城鎮題材。我并不信奉“題材論”,之所以有這么多跳躍,完全是因為我的生活和認知發生了改變,我忠于自己的生活和認知。另外,除了題材上的變換,我在處理環境和人物上也逐漸開闊起來,比如我再也不會把人物安插在某個特定的背景里去寫了,那既不符合生活樣貌,還讓讀者懷疑小說仍沒有一出“舞臺劇”來得寬廣自由嗎?所以,我現在的小說,無論是場景還是人物,他們都是流動的,是活的,是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行為言止的,是有行動力的……當然,我可能做得不夠好,不過方向不會錯。再次謝謝諸位師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