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冷梅|《遠方,不再遙遠》
更新時間:2020-04-28 來源:善美文學(微信公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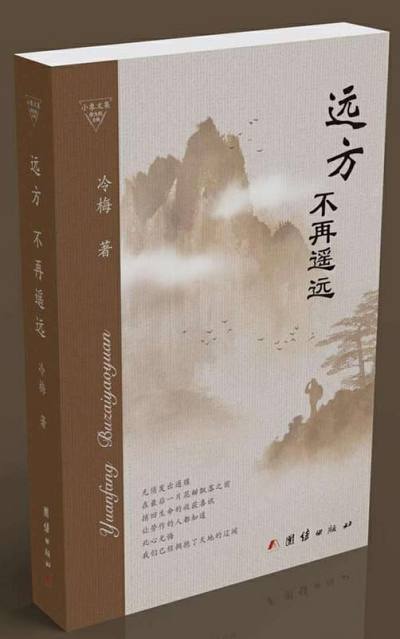
書名:《遠方,不再遙遠》
作者:冷梅
出版社: 團結出版社
出版地:北京
CIP號:2020031402
書號:978-7-5126-7764-7
出版時間:2020年3月
詩集簡介
本詩集的作品,年限跨度較大,既有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作品,又有近年來的新作,只要細細閱讀,便可知其許多詩作是合時而作的,具有較強的時代性。本詩集分為五卷,每卷都有一定分量。冷梅的詩歌“往往于平和中蘊藏一種鋒芒,溫婉里隱隱透出一種力量”。其行吟詩歌既有歷史回音與現代潮聲的交響,又有綠水青山與人文景觀的相互映襯,他深情地俯視著腳下的土地,試圖借助詩歌的力量,營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家園(老刀評語)。
作者簡介
冷梅,知名詩人、作家、詩評家,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廣東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現代作家研究會詩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散文詩學會常務理事、中外散文詩學會理事、汕尾市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數十次在全國詩歌大賽中獲獎,著有文學評論集《請原諒我的淺陋》、詩集《遠方,不再遙遠》、散文詩合集《汕尾九歌》。
附:《遠方,不再遙遠》序言
詩歌,最終是一件與人為善的事情
——序冷梅詩集《遠方,不再遙遠》
老刀
不要猶豫,我的元帥,工兵已蜂擁而出
所有的外敵,都將敗于一縷花香
滿園春色,關不住飛翔的翅翼
沒有什么比我們的追求更加甜蜜
無須發出通牒
在最后一片花瓣飄落之前
捎回生命的收獲喜訊,讓勞作的人都知道
此心無悔,我們已經擁抱了天地的遼闊
——摘自《拼命用幸福包裹自己》
上列詩歌中,蜜蜂是勞動者的化身,作為勞動者一分子的詩人,其追求應是甜蜜的事業。冷梅對待生活和詩歌的態度是一致的。一個詩人的性格可以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不但體現在對待生活、人生的態度上,也反映于詩寫的態度上。一方面是對生命的理解與愛恨的深淺程度,另一方面可以顯示對詩歌抑或是藝術追求的真誠與否。我認為冷梅是一位耿直而倔強的人,不管遭遇多少坎坷曲折,從沒有放棄對詩歌的執著追求。他的首部詩歌集《遠方,不再遙遠》付梓在即,囑余賦序,作為交往多年的好友,自然應允。
冷梅早年的詩歌寫得比較雜,內容包羅萬象,風格也多變,語言比較大氣,但略嫌鋒芒畢露,往往直面社會矛盾和人性缺陷,容易觸及某些人的痛處。閱讀了《遠方,不再遙遠》之后,感覺他的詩風有了較大轉變,口語化寫作明顯淡化,詩歌的思想脈絡不是一目了然,往往于平和中蘊藏一種鋒芒,溫婉里隱隱透出一種力量。
收入本詩集的作品,年限跨度較大,既有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作品,又有近年來的新作,只要細細閱讀,便可知其許多詩作是合時而作的,具有較強的時代性。本詩集分為五卷,每卷都有一定分量。開卷之作《時光交錯》的許多作品寫得非常精致,思想比較深刻,處處拷問人性。《夢向遠方》《大地情懷》的作品融入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教人“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生命回響》是對生命的關注,尤其是反映汶川大地震的作品,讀之感動涕零。《自由飛翔》的作品內容較雜,這也體現了詩人信馬由韁、海闊天空的創作風格。
我們一直關注的生命問題,在冷梅筆下,呈現了平常與一種另類表達。他不是一味抒寫人們的生老病死苦,而是把生命置于戰爭、災難等背景中去考量,被戰爭和災難奪去的生命都是無辜可憐的,通過真誠地詩寫,進而揭示人性缺陷或展現人性光芒。“沒有通往家園的道路,血開始于恐龍時代∕一路染紅花兒,刀劍駕馭憔悴的城邦∕驅趕成群的牛羊,若追逐一粒浮塵那么沉重∥大地顫栗的時候,他們潛入層層濤聲∕打撈出的一截殘骨一枚彈殼,誤以為是香腸和面包∕心中的神沒有拋下救生圈,塵埃簌簌而下”(《大地與塵埃》)。這首詩突破了思維桎梏,視野開闊,家園,戰爭,生命,食糧——這些關乎人類命運的元素,為何在地球上被反反復復提及?其實,人的生命很脆弱,除了人禍的殘害,而一些自然災難的降臨更是令人猝不及防,譬如,印度洋大海嘯、汶川大地震至今令人心有余悸。第四卷《生命回響》集中反映了對珍貴生命的關懷,從另一個側面也體現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注。自古以來,天災人禍總會在不恰當的時間節點在地球的某一個角落爆發,一些生命瞬間成為冤魂屈鬼,而過不了多久,世界又恢復暫時的平靜。
冷梅寫作多年,收入本詩集的應該只是其作品的一部分,無法據此對其創作展開全面的評述評價。但我相信他的創作是與時俱進的,且看《夢向遠方》《大地情懷》這兩卷詩歌,完全符合新時代的新發展理念,處處呈現綠水青山和鄉愁色彩,對祖國的大好河山和一些名城古鎮給予真誠的歌吟,尤其對故園傾注了游子思鄉般的真情。“時光容不得我的太多假設∕就像蝴蝶不能太久的欣賞一株蓮花∕我不得不審視自己,我能為故鄉帶來什么∕除了詩歌還是詩歌,其實故鄉就是一首詩∕一首內涵深刻詩意遼遠的現代詩∕讓我以詩人的名義擁抱你吧∕——海陸豐,我的故鄉”(《故鄉抒懷》)。冷梅的足跡不囿于故鄉,旅痕處處,走南闖北,這或許與他從事過旅游工作有關。豐富的閱歷和經驗,使他對一河一山、一城一鎮、一橋一街,甚或一草一木、一道陽光、一縷花香、一聲牛哞、一抹鷺影……都予以深刻思考和真誠詩寫。故其行吟詩歌既有歷史回音與現代潮聲的交響,又有綠水青山與人文景觀的相互映襯,他深情地俯視著腳下的土地,試圖借助詩歌的力量,營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家園。
冷梅曾是口語化寫作的實踐者,其許多關照弱勢群體和底層命運的詩作,具有口語化寫作的傾向。本詩集也收入一些口語化作品,如《小悅悅死了》《一個瘋子的命運》《6·10祭》《難忘,2008》等作品的口語化特點比較明顯。一直以來,有些人對口語化寫作存在誤解,把那些毫無詩意、粗俗無賴甚至把一句話分行排列的“口水詩”都歸罪于口語化寫作。其實,口語化寫作的特點是語言淺顯易懂,平白中蘊藏詩意,力戒語言拗口、意境平庸或故作高深、嘩眾取寵等詩風,使作品貼近實際,更接地氣。古今中外,能千古傳唱的詩作有不少是口語化寫作的典范,例如,“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樣的詩句,語言通俗且不乏詩意,誰敢說這不是口語化寫作的精品?在此,我只是借為冷梅詩集作序之機,為口語化寫作說幾句話。至于選擇何種詩歌道路,因人而異,不必強求,任何詩歌流派都應有其佳作。相信冷梅也深諳此理。
著名作家鐵凝曾說:“文學最終是一件與人為善的事情。”詩歌作為文學藝術的瑰寶,更應當如此。詩歌更能抒發一個人的感情,也更直接揭示詩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世界豐富多彩,也有其矜持之處,詩人只有奮力深入生活里層和真誠關注人類命運,才有資格窺見那些豐饒的景象,那些靈魂秘密,那些斑斕而多變的色彩,其作品才能充滿生機活力,這是詩歌最終成為一件與人為善的事情的基本前提。無論是歌頌還是鞭撻,詩人都不應該缺席于當下,不能回避現實,并作好隨時發聲的準備。倘若如此達成心靈契約,詩歌最終必是一件與人為善的事情。
扯上以上這些文字,權當為序吧。相信冷梅的詩路會越走越寬,佳作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