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陳劍暉|《潮州傳》:千年歷史遷延中的“城”與“人”
更新時間:2022-03-28 作者:陳劍暉來源:羊城晚報?羊城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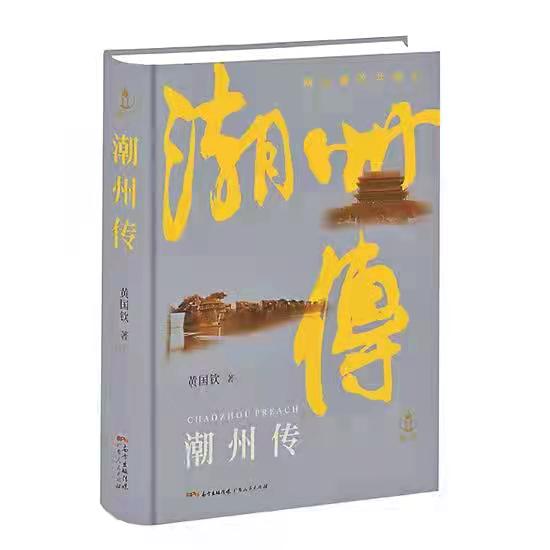
輔以文獻典籍的大散文筆調
近年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城市為單位的地域身份與文化認同為精神指向的城市傳記寫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勢,出現了《南京傳》《北京傳》《上海傳》《海南島傳》《廣州傳》等眾多城市傳記,掀起一股城市傳記的書寫熱潮。
黃國欽的新著《潮州傳》,是眾多城市傳記之后出現的又一部值得關注的作品。
《潮州傳》以非虛構寫作的立場與大散文的筆調,輔以相關歷史文獻典籍,以及近現代以來關于潮州的研究,講述了潮州從遠古時候的一片汪洋大海,發展到新石器時代的浮濱國,再經過千百年興衰沉浮,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歷史文化名城、海上絲綢之路重鎮的歷史進程。
作者追尋潮州的精神源頭,挖掘藏匿于鄉野間的歷史遺存,從城市形態的發展,生活形態、經濟形態與文化形態的變化等方面,重構了我們最熟悉、同時也可能是最陌生的城市——潮州。
全書皇皇46萬字,既有嚴肅的出土文物考證與文獻史料支撐,又有生動活潑、文雅優美的現代表達,在眾多的城市傳記,《潮州傳》堪稱別出心裁的非虛構力作。
個體與歷史的深情對話
個體與歷史的深情對話,是我讀《潮州傳》的第一個感受。“個體”,指的是寫作主體切入城市書寫的視角,以及城市寫作素材的來源與個人經驗,此外還包括城市寫作過程中的表達方式和風格。
而這里的“歷史”,指的是“大史小說”的歷史,它拒絕宏大話語,也不以整體性、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和價值觀為圭臬,而是沉迷于歷史的“邊角料”,注重童年記憶的再現。
在黃國欽看來,“以往潮州的歷史文化書籍,基本上是歷史學者寫的,歷史學者比較嚴謹理性,下筆不帶感情,也不考慮可讀性,而作家只考慮可讀性。”他決意要用帶著個人溫度的紀實手法來寫《潮州傳》,這個傳既要符合史實,考慮到歷史嚴肅性,也要考慮可讀性,盡可能調動讀者的閱讀樂趣。
城市傳記的書寫,與寫作者的精神立場和價值取向有關,即寫作者站在什么位置去把握整個城市,以什么立場去展現和評判這個城市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顯然,《潮州傳》采取的是民間立場,它以平民的視角,讓歷史的細節和民生百態得以充分地展示。
由于黃國欽是土生土長的潮州人,又是作家和對歷史、地理、文學、檔案、新聞等都有所涉獵的文化學者,所以他能夠舉重若輕寫出潮州這座古城獨特的文化形態和這座城市的歲月變遷,又能信手拈來把潮州人的市井生活、民生細節、風俗習性如數家珍地講述出來,如此《潮州傳》自然便有了煙火氣,有一股無法抗拒的親和力。
把城市看作活的生命體
《潮州傳》的成功之處,還在于它把城市看作一個活的生命體——“城”與“人”在千年歷史的遷延中緊密相依,彼此塑形。人創造了城市,而城市也按自己的方式在不斷地生長。
理想的城市傳記應是這樣一種寫作方式:無論是回望歷史,還是立足當下,展現市井生活和民生細節,它一方面將城市視為活的生命體;一方面又以打撈記憶的方式重塑城市傳統,讓人們明白城何以為城,又將在可見的未來如何演進。
應當說,在這方面,《潮州傳》做得相當出色。它既是“傳”,“點”與“面”的結合,歷史的脈絡、時間的線索勾勒得十分清晰,同時又將城市的成長軌跡、性格特征和歷史細節、民生百態融為一體。
《潮州傳》的獨特處,還在于作者將潮州看作一個詩性的潮州,并用文學的筆調,將這個詩性的潮州原汁原味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我們知道,許多城市都有各自的詩性,比如蘇州、成都、廣州,而《潮州傳》所展示的民性與詩性,顯然與上述諸城不同。
由于地少人多,加之天性聰明,不安于現狀,因此潮州人既有蹈險履艱,開拓進取,敢于冒險和超越的一面;又有享受生命,追求精致與閑情逸致,講究詩性的生活方式的一面。
《潮州傳》里的“種田如繡花”“潮州七日紅”“潮音一曲牽人心”等章節,詳細介紹了潮州人如何種田、種水果、刺繡、刻木雕、做陶瓷,以及聽潮劇、品工夫茶,等等。特別在美食方面,潮州人以他們的智慧和巧手,借助一些普通的五谷雜糧,根據不同的口味制成各種小食品,這樣便有了著名的“潮州美食”。
的確,很少見到一個地方,能如此地將豪放與精致,華美與內斂,開拓冒險與詩性地感受生活,享受生命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種詩性氣質已經滲透到了潮州的骨髓里,并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不同于別地別城的潮汕文化精神。
城市傳記寫作“熱”將持續
城市傳記作為一種非虛構寫作,它兼具歷史與文學的雙重屬性。美國學者米爾斯在其名著《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倡導學者個人的生命體驗,他認為生命體驗對于城市的學術研究極為重要。因為城市本身,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構成的,而真正有價值的城市史研究,不應該只是冷冰冰的學術表述,而應帶著作者個人情感的投射與生命的體溫。
黃國欽在創作談中提到:“‘文章不是無情物’。寫文章要投入感情,先感動自己,才能感動讀者。比如寫到宋末元初,文天祥、陸秀夫在潮汕抗元的故事時,我是含著熱淚在寫作。”
的確,城市不是沒有生氣的冷冰冰鋼筋水泥體,而是承載了無數悲歡離合的生命體。由于《潮州傳》深入到城市的內在紋理,作者飽蘸著感情,一方面希望最大限度地回到歷史的原點,寫出潮州這座城市的性格與獨特風物;另一方面又立志要為這座城市的平民生活和普通民眾立傳。
這樣,《潮州傳》便呈現出獨特的書寫立場和精神空間。它既是潮州人的精神族譜,也是一部有溫度的非虛構作品。
城市傳記的寫作方興未艾。可以預期,這股源于彼得·阿克羅伊《倫敦傳》的城市傳記書寫熱,在中國還會持續“熱”下去。因為在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城與人,城與家,城與國的多重聯系中,具有非虛構特質的城市傳記書寫,已在個體與歷史的深情對話中,呈現出城市文明的演進歷程,并打開了廣闊的城市精神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