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biāo)題

標(biāo)題
內(nèi)容
首頁(yè) > 粵評(píng)粵好 > 批評(píng)進(jìn)行時(shí)
向衛(wèi)國(guó)丨“隨水而來(lái)”的物質(zhì)想象或精神追蹤
更新時(shí)間:2022-10-31 作者:向衛(wèi)國(guó)來(lái)源:南方農(nóng)村報(bào)
1
在西籬的自傳性長(zhǎng)篇小說(shuō)《晝的紫夜的白》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那一段茂盛、藥香濃郁的野菊花,像在列隊(duì)歡迎她。她想為它們歌唱,沒(méi)來(lái)得及發(fā)聲,疼痛就像雷電一樣快捷,令她支撐不了自己,倒下,在野菊花叢中,下午四點(diǎn)整,生下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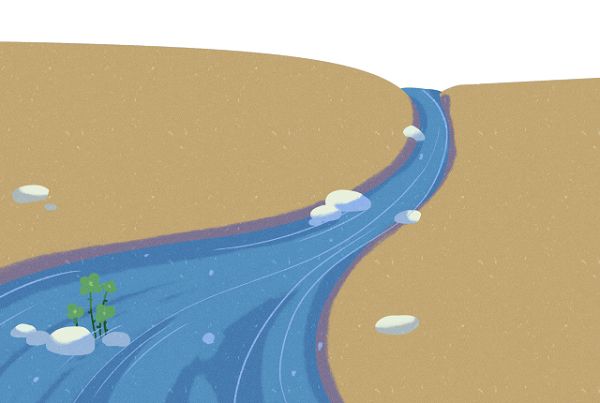
生命就是一趟隨水而來(lái),又隨水而去的旅程。
小說(shuō)的自傳性及第一人稱(chēng)敘述的方式,會(huì)讓人自然認(rèn)為小說(shuō)中的“我”就是詩(shī)人西籬,或者至少是西籬想象之中的另一個(gè)更本原性的“西籬”。
作為讀者,在我看來(lái),這一段文字同時(shí)提供了西籬詩(shī)歌中兩個(gè)原型性質(zhì)的物質(zhì)元素或物質(zhì)想象——水和植物(花)——的原始性來(lái)源。因此,西籬最近的詩(shī)集名曰《隨水而來(lái)》,詩(shī)集中乃至她全部詩(shī)歌中最重要的詩(shī)作也是長(zhǎng)詩(shī)《隨水而來(lái)》。
2
西籬名字為其父所賜,得于陶詩(shī)“采菊東籬下”的另一版本“采菊西籬下”。她16歲考入貴州大學(xué)中文系,美麗的花溪滋養(yǎng)了她的生命,同時(shí)激發(fā)了她最初的詩(shī)情。她在《懷念花溪》里吟唱——?
四月金黃的花海
就在溪畔生長(zhǎng)
直長(zhǎng)到貼近藍(lán)色的天空
愛(ài)夢(mèng)的女孩
就在花蕊的中央做夢(mèng)大學(xué)階段對(duì)任何一個(gè)人來(lái)說(shuō)都是生命的重要驛站,它是除童年之外,滋養(yǎng)生命和夢(mèng)想成長(zhǎng)的另一個(gè)浪漫和幻想之域,自此以后,社會(huì)將會(huì)給予人生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教育。多年之后,當(dāng)詩(shī)人再次回憶花溪,“花”與“溪”仍然是最重要的夢(mèng)想元素,由它們所滋育的情感亦再次化育為詩(shī)歌和愛(ài)情:
我想知道
還有沒(méi)有另外的人
和我一樣
在這美麗的水邊成長(zhǎng)
如果是五月
綿綿細(xì)雨就會(huì)漲滿她的心房
漲滿她戀愛(ài)的愿望
西籬大學(xué)畢業(yè)之后,在文學(xué)月刊《花溪》作為文學(xué)編輯工作了一些年,但最終她離開(kāi)了,去到更遙遠(yuǎn)的南方羊城定居。“隨水而來(lái)”是從旅途的終點(diǎn)來(lái)看,如果從起點(diǎn)看,就是“隨水而去”:“我知道/即使寒冬降臨 大雪紛飛/花溪也依然碧綠/運(yùn)載著朵朵雪花/流向遠(yuǎn)方……”
可以說(shuō)是花溪的水把她載向遠(yuǎn)方,但更為本質(zhì)的,是一種如煙雨一般朦朧的夢(mèng)想,帶走了她。流水和煙雨,始終如一種情緒的云霧,盤(pán)繞在她的詩(shī)歌中,這一點(diǎn)已有論者指出過(guò)。
?3
從精神分析學(xué)的角度來(lái)看,“隨水而來(lái)”的動(dòng)態(tài)形象,決不是一個(gè)隨便的命名,它既是個(gè)體也是一個(gè)生命的集體原型或者關(guān)乎生命來(lái)源的隱喻。
隨水而來(lái)
它無(wú)聲無(wú)息卻長(zhǎng)驅(qū)直入
在它洶涌之峰的上部
日光閃爍的地方
生活
正消融其實(shí)有的一切
? ? ? ? ? ? ? ? ?——《隨水而來(lái)》?
當(dāng)現(xiàn)實(shí)中的一切隨著時(shí)間和個(gè)人生命的悟入而逐漸“消融”,失去它的實(shí)有性,反轉(zhuǎn)為虛幻的夢(mèng)境時(shí),生命又再次聽(tīng)到甚至是看到那流水,那承送著生命來(lái)去的最初的水。于西籬而言,水不僅是送來(lái)生命的使者,也是運(yùn)送生命去往遠(yuǎn)方的航船,人的一生逐水而來(lái),跨水而去,最后又回到原始的水和植物。
噢 水們漫過(guò)街道
然后毫無(wú)動(dòng)靜
石頭爆裂的聲音
將在明天響起
無(wú)論如何
我也得跨過(guò)這水……
? ? ? ? ? ? ? ? ? ? ? ——《水》?
讓人疑惑的是,西籬有寫(xiě)給父親的詩(shī)《父親》,而母親的形象在她的詩(shī)歌中基本是缺席的,只偶爾會(huì)泛指性地出現(xiàn)“母親”這個(gè)詞。西籬的傳記小說(shuō)《晝的紫夜的白》講述的就是一個(gè)“尋找母親”的故事:“我”的母親在生下我后不久音訊杳無(wú),成為一個(gè)理論上永恒的失蹤者。所以,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只是一種想象和意念,并不能轉(zhuǎn)化成具體的詩(shī)歌實(shí)體意象。在這個(gè)意義上講,母親和“隨水而去”的“水”一樣,都是無(wú)法完成塑形的深層物質(zhì)或元素。
4
在西籬的詩(shī)歌中,反復(fù)出現(xiàn)過(guò)以植物(尤其是花)自喻的詩(shī)句。也就是說(shuō),植物或花在西籬詩(shī)中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外在的情感對(duì)象和詩(shī)歌意境的構(gòu)成因素而存在,而是更為內(nèi)在和深刻的生命元素,或?qū)⑸没挠麑?duì)象。這或許因?yàn)閺脑匦缘摹八敝姓Q生出來(lái)的最原始生命形象就是植物(微生物雖然是更早的生命,但它不在人的視覺(jué)范圍之內(nèi),無(wú)法成為生命感知的對(duì)象,從而也自古就缺席于心理、藝術(shù)的意象世界)。從詩(shī)人在自傳小說(shuō)的虛擬和想象中,將“自我”誕生于花叢(也許本來(lái)就是真實(shí)的寫(xiě)照),以及在“鄉(xiāng)下”的大自然中最初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到花溪兩岸四季數(shù)不清的花朵對(duì)詩(shī)人的視覺(jué)、嗅覺(jué)和情感夢(mèng)境的長(zhǎng)年浸潤(rùn),不同時(shí)期帶有共性的知覺(jué)想象因素,使得詩(shī)人幾乎終身都有一種將自我的生命植物化的沖動(dòng),或許這原本也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和藝術(shù)中,將一切主體都進(jìn)行自然化處理的傾向在現(xiàn)代詩(shī)歌中的隱性存在。
把自己看作翠綠的植物
我們來(lái)自鄉(xiāng)間? 那時(shí)十六歲
? ? ? ? ? ? ? ? ? ? ? ?——《溫柔的沉默》?
他關(guān)注的孩子
是雨水一樣的花朵
谷粒一樣寧?kù)o
? ? ? ? ? ? ——《溫柔的沉默》?
望那我們想的地方
像兩朵花一樣
? ? ? ? ? ? ?——《夢(mèng)歌》?
我們雙雙躺著
像兩朵小小的淺淺的花
? ? ? ? ? ? ? ——《夢(mèng)歌》?
而我,是屋子里的某一角
一株淡金色的植物
? ? ? ? ? ? ? ?——《屋子里再不會(huì)有人來(lái)了》?
?除了作為一朵花
一株自然的植物
你又還是什么呢?
? ? ? ? ? ? ? ——《隨水而來(lái)》?
上述類(lèi)似詩(shī)句的反復(fù)出現(xiàn),有如某些基本的夢(mèng)境,常常伴隨某個(gè)人的一生,它并不是沒(méi)有來(lái)由的,一個(gè)詩(shī)人對(duì)“自我”的沉浸和對(duì)自我生命來(lái)歷的追問(wèn),有時(shí)比哲學(xué)家更為迫切和顯得更為生命攸關(guān)。而母親實(shí)體形象的缺失,這種非常特殊的個(gè)體生命遭遇或命運(yùn),或許也會(huì)導(dǎo)致人在找尋自我生命來(lái)源的時(shí)候,在潛意識(shí)或者不自覺(jué)的幻像生成中,以自我認(rèn)同或熱愛(ài)的另外的形象,暗中實(shí)施了生命的物質(zhì)元素和生命誕生的場(chǎng)景置換。
5
水和植物,這兩種物質(zhì)形象的另一個(gè)無(wú)意識(shí)的衍生形象,是語(yǔ)言和詩(shī)句本身。從詞語(yǔ)到詩(shī)句的生長(zhǎng)、流動(dòng),直到最終成為一首完整的詩(shī)的過(guò)程,也十分類(lèi)似于或完全可以類(lèi)比于在水的滋養(yǎng)下,一株植物從發(fā)芽、伸展出枝葉,到最后長(zhǎng)成植株的過(guò)程。我們有理由認(rèn)為,詩(shī)人對(duì)此是有一定的意識(shí)覺(jué)醒甚至自覺(jué)認(rèn)知的。
讓我們?cè)俅位氐交ㄏ?/span>
我在十月南方的人流之中
抬頭看見(jiàn)天邊的花溪
那風(fēng)和陽(yáng)光的聲音將詩(shī)歌吟唱
心靈在清澈之中開(kāi)始激蕩
? ? ? ? ? ? ? ? ? ? ? ?——《懷念花溪》?
在那詩(shī)人幻想的“天邊的花溪”,詩(shī)句被“風(fēng)和陽(yáng)光的聲音”自然地吟唱出來(lái),顯然這詩(shī)就像花溪的水和花一樣,是大自然本身的產(chǎn)品。因此,水和植物的物質(zhì)形象,不僅是個(gè)體生命所希望的幻化對(duì)象,在詩(shī)人的想象中,也是詩(shī)歌和詩(shī)句的語(yǔ)言形象之隱秘的或心理上的物質(zhì)前身。
更為深入而具有多種綜合意向的詩(shī)句是下面的這一段,詩(shī)人顯然是將主體的水、植物、“我”和語(yǔ)詞構(gòu)成的詩(shī)句等四種物質(zhì)形象,同時(shí)幻化為一了:
即使明天的我
只是些如水的詩(shī)行
對(duì)奇跡永遠(yuǎn)的追逐
已在生命里布滿了輝煌
我生長(zhǎng)在那一片金色之中
那秋日的凈土安寧而芬芳
? ? ? ? ? ? ? ? ? ? ——《我守在那一片金色之中》?
在這一段詩(shī)中,“植物”元素,雖然沒(méi)有直接出現(xiàn),但那一片“輝煌”的“金色”顯然就是詩(shī)人多次自喻的植物形象。至于為什么詩(shī)人渴望成為的植物,都是“金色”或“淡金色”,必然會(huì)再次讓我們想起她誕生于金色的野菊花時(shí)那個(gè)生命的偉大場(chǎng)景;存在于詩(shī)人深層意識(shí)中的那個(gè)“金發(fā)的嬰兒”(《雨的夜歌》),必定是披散著金色花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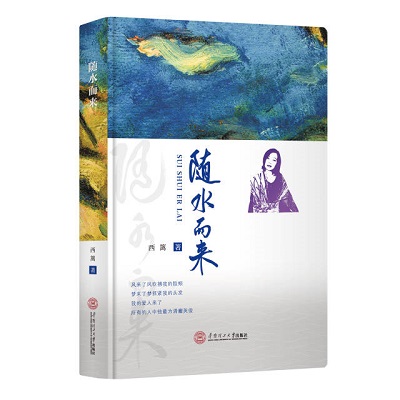
《隨水而來(lái)》,西籬著,華南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