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標題
內容
粵派評論 | 打工文學:源于廣東,在世界文學譜系里尋找一席之地
更新時間:2023-07-06 來源:羊城晚報?羊城派
近些年來,許多基層打工者一邊打工一邊進行文學創作,包括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王計兵的《趕時間的人》,以及大量活躍在網絡上的“野生詩人”的作品,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據悉,僅快手、B站、小紅書三個平臺上寫詩的人就超過百萬,“一年有360天與機器相處,詩里卻有山川湖海”——

6月28日,以“新的‘打工文學’在崛起?”為主題的“粵派評論”文化沙龍在羊城創意產業園金羊網演播廳舉辦,相關專家學者聚談“打工文學”的內涵、當下的意義和未來的前景。
參與沙龍活動的嘉賓有: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蔣述卓,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深圳大學客座教授楊宏海,《作品》雜志社社長、總編輯王十月,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柳冬嫵,《我在北京送快遞》作者胡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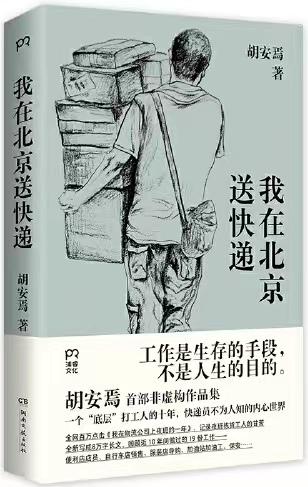
從廣東起步,影響遍及世界
羊城晚報:關于“打工文學”的概念,一直有爭議,到底該如何界定“打工文學”?這么多年過去,“打工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都有哪些變化?
楊宏海:“打工文學”概念的提出源于當年深圳的改革開放實踐和文化建設實踐。上世紀80年代,我有機會在當時深圳的各個文化現場做調查研究。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外來打工者到深圳,他們大量的時間是在工地、車間流水線上,非常緊張,但是當時的深圳還沒有更多的文化生活場所提供給他們。作為年輕人,他們覺得自己白天是“機器人”,晚上是“木頭人”,生活枯燥。逐漸地,在打工青年當中,有一批喜愛文學的年輕人,就開始在工余時間拿起筆寫他們心中的感受。我在蛇口工業區的三洋廠調研時,發現廁所里密密麻麻寫著打工青年自己創作的歌謠,很震撼,可以說我在這里發現了第一首打工詩歌。
1984年《特區文學》第三期有一篇短篇小說是林堅寫的,叫《深夜,海邊有一個人》,寫農民工青年進入城市之后,在工業文明與傳統農業文明產生沖突的背景下,他們與現代企業產生了矛盾和抗爭。這在我的印象中是一種全新的文學表達,我個人認為它是第一篇打工題材作品,后來我把這篇小說定位為“打工文學”的開山之作。還有,打工青年張偉明寫的《下一站》,也非常精彩。
我意識到可能有一種新的文學形態已經出現了。那么,這種新的文學形態是什么?一開始還沒有被命名為“打工文學”,普遍的叫法是“打工仔文學”。因此,我提出了“打工文學”的概念,就是寫打工者的文學、打工者書寫的文學,但也不排除文人作家的創作,比如陳秉安的《來自女兒國的報告》、陳榮光的中篇小說《老板·女工們》。
現在30多年過去了,“打工文學”實際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打工者群體的年齡結構、審美特征、行業特征都發生了變化,現在的打工一族已經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工廠車間流水線,比如我們現在比較熟知的快遞員、滴滴司機等一批人,甚至包括了工廠的高管、技術人員、碼農,還有不同行業自稱為打工者的人。
柳冬嫵:我是這樣理解的,廣義的“打工文學”就是指所有寫打工題材的文學作品;狹義的“打工文學”就是有著打工經驗的人所寫的打工題材的文學作品。莫言曾經提出關于打工文學的界定,我感覺莫言的說法是非常好的。他說最好的打工文學是有打工經驗的人寫出來的,專業作家也可以寫打工文學,也可以發表,看起來也像那么回事,但是在關鍵的時候,看起來是“假”的。
蔣述卓:“打工文學”主要是得自于廣東改革開放、容納全國各地的青年來廣東打工和創業的環境和現實。在打工之余,他們自發產生了這樣一種創作。2005年的時候,在增城舉辦了一次全國性的“打工文學”頒獎活動,當時也叫“進城務工文學”,后來在佛山又舉辦了一次“打工文學”的頒獎活動,當時叫“新產業工人文學”,概括面更大,其他一些從事個體職業的,包括網絡寫作,都可以包含在里面。
在“打工文學”中,產生了許多優秀作家作品,像王十月的《國家訂單》,獲得魯迅文學獎,這也是在“打工文學”領域里廣東文學得到的最高獎項。鄭小瓊所寫的《黃麻嶺》等詩歌,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還被翻譯成了多國文字,這也進一步擴大了“打工文學”的影響力。
“打工文學”的特征,就是以打工者的親身體驗書寫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包括打工過程中所經歷的某種疼痛感,生活的真切感,還有與工廠一塊成長的經歷;第二個特征是它以一種全新的內容和體驗,給文學界帶來了新氣象。

是否屬于“打工文學”沒有標準答案
羊城晚報:能否從創作者的角度談談對“打工文學”的理解?
王十月:“打工文學”的命名已經約定俗成了,再去爭論命名沒有必要。我經常說“打工文學”就像是我身上的一個胎記,我就是這樣過來的,我就是這樣開始寫作的,所以作為寫作者,我不會刻意去在乎我是誰,要想的是我是否準確把握、表達了我所知道的這個時代。
我寫了這么多年,不認為“打工文學”標簽是一個壞事,反而于寫作者而言是有幫助的,但是我也不會主動擁抱它。這個標簽會局限讀者和研究者對你作品的解讀,但一個真正有抱負的作家,寫作真的足夠開闊,自然而然地人家會發現你的另外一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是非常感謝這樣一個標簽的。一個作家被貼上標簽,再失去這個標簽或者再貼上更多標簽的過程,就是一個寫作者自我豐富的過程。
胡安焉:其實我之前對“打工文學”是并不了解的,雖然我已經寫作了十幾年,但是在2020年之前,我的寫作方向主要是小說,而它并不都是從我的職業經歷里面取材的,所以在這之前我覺得“打工文學”這個說法和我是沒什么關系的。
但是因為今年我出版了一本非虛構文集,書名就叫做《我在北京送快遞》,于是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里,確實好幾次有人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了,所以我開始去想“打工文學”跟我的關系。我自己認為這本書其實更接近于一個人的回憶錄,當然它是圍繞我的工作經歷來講述的。所以假如它被歸為“打工文學”的其中一本作品,我當然是能夠理解和接受的。但我覺得這種歸類方法,可能主要還是從讀者、研究者、傳播者或者出版方的角度出發的。而作為寫作者,我其實從來就沒有懷著要寫“打工文學”這樣的意圖和意識。我覺得文學前面加的定語越多,受到的削減和局限就越大,當然我也能理解,出于研究的目的,這些局限有時候是必須的。
所以我能理解“打工文學”這樣的概念,但它從來不是、也不會成為我自主的寫作意識。假如有人問我,你是不是在寫“打工文學”,我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假如是這樣問,你寫出來的是不是“打工文學”?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就跟我本人無關了,它可能既沒有也不需要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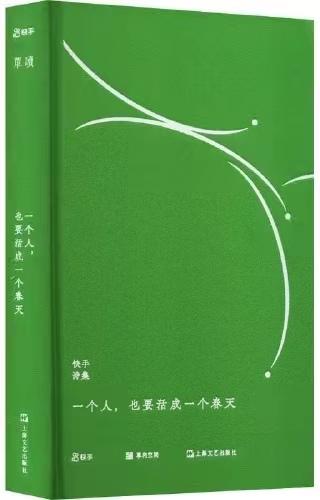
和莫言、余華、賈平凹“同臺競技”?
羊城晚報:文學在你們的“打工”時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當時為什么會提起筆來進行創作?
王十月:說到寫作,我的出發點其實非常簡單,從小喜歡閱讀,后來在工廠里面打工的時候,因為初中沒有畢業,我不想做一個流水線上的工人,也不想學一門技術。后來聽說了周崇賢和安子通過寫作也過得不錯,我就去買他們的書,然后發現這種作品我也可以寫,然后慢慢就走上寫作這條道路。
我寫作半年時間不到,就從工廠出來成為一名編輯,這個時候我意識到我要做另外的事。當時,大家對于“打工文學”的討論,我明顯感覺到有一些歧視,所以我就想寫出好的作品讓“打工文學”變得“入流”。我當時希望跟莫言、余華、賈平凹等人“同臺競技”,不因是一個打工仔而受到歧視或者優待。但是寫了很多年后,我發現這樣的想法也比較幼稚,因為這些都背離了文學的本質,其實文學更多是我跟世界對話的工具,我心中真正偉大的作品也是跟世界在對話、在交流,重要的是你在這個世界發現了什么。
后來寫到《國家訂單》,很多評論家對這部作品有很宏觀的解讀,看到了中國也看到了世界,但是我寫的時候并沒有這些觀念,我想寫的只是全球化時代,發生在一群普通中國人命運中的一種蝴蝶效應。
胡安焉:我是從2009年開始寫作的,當時我已經30歲了,在那之前我的社會經歷應該說是過得不太順利的,有比較多的痛苦和不適應。寫作對我來說,其實就是一條精神出路,它首先是一件創造性的事情,這種創造性是建立在個人的獨特性之上的,就沒有兩個人會寫出完全一樣的作品,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人。
從我個人的社會經歷而言,今天社會生產的分工模式里,其實每個人都是可以被替代的,比如說像富士康的流水線工人,誰去做效果都是差不多的。現代化的生產某種程度上抹平了人與人的差異,弱化了人的個性。寫作其實也是對我在工作中付出的這些代價的一種補償,因為在寫作里我是獨一無二的,如果沒有這種獨一無二的話,我就相當于沒有存在過一樣。
但寫作不是我主要的部分,我現在被很多人關注確實是因為“打工文學”這個標簽,如同王十月老師所說,它可能是命運給我的一種饋贈,讓我有機會能夠抵達更多的讀者,我確實應該感到慶幸,有這個機會的話,我以后的寫作也會有更豐富、更多元的發展。
需關注新的生產關系和生活經驗
羊城晚報:“打工文學”創作在當下有怎樣的新態勢?
楊宏海:今天跟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整個社會的生產力、科技發展水平以及工人的職業特征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這幾年來又有疫情,經濟結構也發生了變化,所以在我們相當多的行業當中,打工人、“打工文學”又興起了,成為一個新的關注點,這些新的平臺、新的經驗也讓“打工文學”在原來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
由此我感覺新的“打工文學”,必須要去關注這種新的社會生產關系的變化。比方說現在機器人時代就要來臨,那么相當多的打工人可能就面臨著新的命運了,有沒有比較敏感的能夠進入生活而且能反映這種生活的作品作家出現,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柳冬嫵:根據我的觀察,廣東或者說中國的“打工文學”,可能從類型化的角度看得越細,對它幾十年的發展會更清楚。比如說打工文學,我們可以把它進一步細分為打工詩歌、打工小說、打工散文,因為不同的文體所呈現出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樣的。比如,曾楚橋在《收獲》上發表過一部小說《幸福咒》,整個小說系統結構性的反諷,完全具備后現代小說的一些典型特征;打工詩歌出現了很多優秀的詩人,這可能是廣東對中國詩歌的一個重要貢獻。
蔣述卓:以我有限的認知來看,目前為止,廣東文學引起國際上關注度最高的是“打工文學”。這幾年來一直有海外的一些學者來找我,要探討“打工文學”“打工詩歌”,比如,荷蘭萊頓大學教授柯雷,他專門研究了這一塊,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很多外國人把中國的勞工當作觀察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窗口。
當下打工的范圍越來越寬泛,不再限于過去的某種職業。像今天的物流業、快遞業,還有出租車司機、大橋建設者等,由此“打工文學”書寫的范圍也會越來越廣,越來越有前途,在新的時代可能具備新的品質,新的書寫方式。“打工文學”的創作者本身由于素質的提升,他們的創作也會有一些新的特質。
大灣區為創作提供更廣闊空間
羊城晚報:有人認為“打工文學”是離文學本質最近的文學樣式,從生活中來,有血有肉,帶著創作者的真情實感。這樣的文學在當下有什么特別價值和意義?
蔣述卓:文學要真,不僅要貼近生活,讓老百姓感覺到有血有肉,還要能夠引起共鳴。那么這種真實就恰恰能夠反映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變化,就像當年的杜甫的現實主義詩歌寫作一樣,他才成為偉大的詩人。
第二,文學在發展,“打工文學”也需要不斷提升,包括寫作的技巧,很多人可能有了后現代的寫法,也有先鋒小說的寫法,也有了更多跟國際接軌的一些寫法,這是完全可以達到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改變“打工文學”不太上層次的觀念,一種文學樣式能夠真正貼近時代表現人心,能夠真正成為老百姓所喜歡的文學,它就是文學的經典。
柳冬嫵:“打工文學”最為寶貴的品質是它的真實性,希望“打工文學”也要關注善和美。未來“打工文學”可能賦予中國文學一個世界性的因素,因為它是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產物,它不僅是廣東的產物,中國的產物,它在世界文學史上都能找出自身的譜系來。其實,19世紀中葉,英國就出現了工業小說,法國的文學里面也出現了大量的女工形象,包括美國文學、芝加哥文學都有類似的書寫,當下中國的“打工文學”和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有待學術界進一步探討。
王十月:俄羅斯著名漢學家奧洛夫在研究“打工文學”時,談到為什么他們會關注這一類作品,是因為他們從這些作品中看到了中國夢,這個中國夢是指中國人夢想過上怎樣的生活,以及為了過上夢想中的生活付出了怎樣的努力和代價。我認為這其實就是文學很重要的主題。
胡安焉:接下來我的寫作可能會回到小說方向,因為我之前寫自己的工作經歷基本都寫完了。我過往的寫作基本都是中短篇,還沒有寫過長篇小說,我想通過一次長篇的寫作去突破一些問題。
蔣述卓:粵港澳大灣區給文學創作,也包括“打工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更加廣闊的空間和發展的背景,希望“打工文學”未來能夠有更好的提升,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新時代進程中的一個鮮明的標志。

2023年7月2日《羊城晚報》A6廣角版